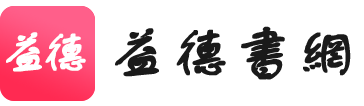華特‧韓德森九歲的時候,有好一陣子覺得倒下去死掉是全世界最浪漫的事,他幾個朋友也有同感。他們發現,玩警察抓小偷的遊戲唯一令人滿足的一刻是假裝中槍,揪著心口,放掉手上的手槍然後倒在地上。沒多久,大家把其他部分都省了煩人的選邊和逃跑只留下遊戲最精華的部分。之後這演變成一種獨角戲,幾乎是一項藝術。其中一個男孩還會戲劇性地沿著山坡頂跑,然後埋伏的人在某一刻出現:玩具手槍同時瞄準,一陣整齊的喉音大喊出斷斷續續、有點粗啞的砰!砰!一小男孩模仿槍聲。演出者就停下來、轉身,痛苦而優雅地站了一會兒,往前倒下去並沿著山坡向下滾,手腳捲起一陣壯觀的塵土,最後四肢攤平在山下,成了一具死屍。當他站起來把塵土拍掉,其他人就評論他的表現(相當不錯、太僵硬或看起來不太自然),接著換下一個演員。遊戲就這樣而已,但華特‧韓德森愛極了。他是個瘦小而四肢不協調的男孩,這是唯一一種勉強稱之為運動而他相當在行的事情。沒人比得上瘦弱的他奮不顧身滾下山的模樣,他沉浸在眾人給予的小小喝采。幾個年紀較大的男生把他們嘲笑了一頓,其他人終於對遊戲厭煩;華特心不甘情不願地改玩對身心有益的遊戲,沒多久便把這件事給忘了。
但在將近二十五年後的一個五月下午,他又記憶鮮明地想起。這時他在萊辛頓大道上一間辦公室裡,坐在辦公桌前假裝辦公,等著被開除。他已經長成一個嚴肅而態度熱忱的年輕人,衣著看得出東岸大學的影響,頂上整齊的棕髮正要開始稀疏。多年來的健康讓他不再那麼瘦弱,雖然四肢仍然不協調,但現在只有在小地方才看得出來,比如他在整理帽子、皮夾、劇院票和零錢的時候,老婆一定得停下來等他,或是看到門上寫著拉但往往用力去推。無論如何,此刻的他坐在辦公室裡,看起來還是一副精神健全又稱職的模樣。沒有人料得到焦慮的冷汗在他的襯衫底下往下流,也不知道他藏在口袋裡的左手手指正撕著捏著,慢慢把一包火柴變成濕潤的紙漿球。這幾個禮拜以來他逐漸有預感,今早一踏出電梯,立刻感覺事情會發生在今天。幾個上司說早啊,華特的時候,他看見對方的笑容裡隱藏了一絲擔憂;然後下午他從自己工作的小隔間缺口抬頭望出去,剛好和部門經理喬治‧克洛維爾四目相交,他手裡正拿著幾張紙,躊躇地站在私人辦公室的門口。克洛維爾立刻轉過頭,但華特知道他一直在看他,為難但已下定決心。再過幾分鐘,華特確信,克洛維爾就會叫他進去宣布壞消息當然不是容易的事,因為克洛維爾這種老闆是以身為普通人為榮的。現在不能做什麼,只能等著事情發生,盡可能溫文儒雅地接受。
就在這時那段兒時回憶開始侵蝕他的心,因為他忽然發現那股力量強大到讓他的拇指指甲深深摳入那包祕密的火柴讓事情發生並溫文儒雅地接受,可說就是他的生活模式。不可否認,有風度的輸家這種角色,向來深深吸引著他。他用整個青少年時期練就這項專長,打架時勇敢地輸給比自己還壯的男孩,足球踢得很爛,暗地裡希望受傷被抬到場外(有一點不得不佩服韓德森,學校教練曾經說笑,這小子還真愛找苦頭吃。)大學有更多機會讓他展現這項才能等著被當的課、等著落選的選舉之後的空軍讓他以空軍軍校學生的身分被光榮地刷掉。這一次看似無可避免,他又要做自己了。之前的幾份工作都屬於初階性質,不容易搞砸;當他有機會出任這份工作之後,套一句克洛維爾的話,感覺起來是真正的挑戰。
很好,華特當時說。這就是我要的。他把這段對話告訴妻子,她的回答是:噢,太好了!他們還藉機搬進東六十幾街的昂貴公寓。近來他開始帶著疲憊的臉色回家,陰鬱地說他懷疑自己還能撐多久,她便囑咐孩子們別煩他(爹地今天晚上很累),給他送上一杯飲料,小心翼翼地給他做太太的撫慰,盡可能藏起自己的恐懼,從來不去想、或至少不表現出來她面對的是一個習慣且強迫性的失敗者,一個喜歡倒下去的奇怪小男孩。最不可思議的是,他心想這真的是不可思議他從前竟然都沒想過。
華特?
小隔間的門推開,喬治‧克洛維爾站著,看上去很不自在。你到我辦公室來一下好嗎?
好的,喬治。華特跟著他走出小隔間,經過整間辦公室,感覺到許多眼光投在他背上。自重一點,他告訴自己。最重要的是保持自重。然後門在他們背後關上,克洛維爾鋪了地毯寂靜無聲的私人辦公室裡現在只有他倆。二十一樓之下,刺耳的汽車喇叭聲聽起來很遙遠;其他只聽得見彼此的呼吸聲、克洛維爾走到辦公桌時皮鞋的吱嘎聲,以及他坐下時旋轉椅發出的咯吱聲。拉張椅子坐,華特,他說。抽菸嗎?
不了,謝謝。華特坐下,雙手緊緊交叉放在膝蓋間。
克洛維爾沒替自己拿一支菸就關上菸盒,把它推到一旁,然後身體向前,兩手攤開平放在桌面的厚玻璃上。華特,我還是直說吧,他說,最後一絲希望消失無蹤。有趣的是即便如此,聽到還是震驚。哈維先生和我觀察了一段時間,感覺你不太能掌握這裡的工作。我們兩個都萬分不願意,但對公司和對你本人最好的情形下,還是要請你走路。那麼,他很快接著說:這完全無關個人,華特。我們這裡的工作太專業,無法要求每個人在工作上表現優異。尤其在你的例子,我們真的覺得你去別的機構會更快樂,比較符合你的能力。
克洛維爾往後靠,舉起雙手的時候,濕氣在桌面留下兩個完美的灰色手印,像骷髏的手。華特盯著看,入了迷,直到手印乾掉消失。
嗯,他說,抬起頭。喬治,你說得非常婉轉,謝謝。
克洛維爾的嘴唇正擠出一個帶著歉意的普通人微笑。非常遺憾,他說。事情有時候就是這樣。接著他開始摸索抽屜把手,明顯看得出鬆了一口氣。那麼,他說,我們開了一張支票,你的薪水付到下個月底為止。可以算是遣散費吧在你找到下一份工作之前幫你度過這段期間。他拿出了一個長信封。
你們太慷慨了,華特說。然後是一陣沉默,華特明白要由他打破沉默。他站起來。好的,喬治。我不耽擱你了。
克洛維爾很快站起來,伸出兩隻手走到桌子另一邊,一隻和華特握手,另一隻手放在他肩膀上,一路走到門口。這個既友善又羞辱的舉動,瞬間讓華特的喉頭哽住,有那麼可怕的一秒鐘他以為自己快哭了。好了小子,克洛維爾說,祝你好運。
謝謝,他說,聽見自己穩定的聲音讓他鬆了一口氣,以至於他又笑著說了一次。謝謝,再見,喬治。
回到他的小隔間有一段大約五十呎的距離,華特‧韓德森很有格調地走完。他知道自己遠去的肩膀在克洛維爾眼中是那麼平穩挺直,他也知道當他經過各個辦公桌,坐著的人羞怯地抬頭或想而沒有抬頭,他是如何精密地控制自己臉上的表情。彷彿就像電影裡的一幕。攝影機從克洛維爾的觀點開始拍,然後以推軌方式往後讓整個辦公室入鏡,框住華特孤寂但莊重的路程;現在是華特的臉部特寫,跳接到他同事轉頭的短鏡頭(喬‧考林斯面帶擔憂,佛列德‧赫姆斯壓抑著心中的竊喜),然後再剪到華特的觀點,我們看到他的祕書瑪麗,臉上尋常而不帶懷疑的表情,她拿著一份華特交代她打的報告,站在他的辦公桌旁等他。
我希望這樣還可以,韓德森先生。
華特接過之後丟在桌上。沒關係了,瑪麗,他說。聽著,你乾脆今天休息吧,明天早上再去找人事室經理。你會被安排新的工作,我被開除了。
她的第一個表情是個淺淺、帶著懷疑的微笑她以為他在開玩笑接著便臉色蒼白開始發抖。她很年輕,不太機靈;祕書學校可能沒跟她們說過,上司也是會被開除的。怎麼會這樣,太糟糕了,韓德森先生。我他們怎麼會做出這種事情?
噢,我也不知道,他說。很多理由吧,我想。他開始清理私人物品,打開抽屜後猛地關上。東西不多:一些舊的私人信件,一支乾掉的鋼筆,一個打火石用完的打火機,半條包起來的巧克力棒。她看著他把東西整理出來放進口袋,他知道每一件物品在她眼裡看起來有多辛酸,他也知道自己如何莊重地直起身子、轉過去,從架上拿起他的帽子戴上。
當然,這不會影響你,瑪麗,他說。到早上公司會幫你安排新工作。那麼,他伸出手。祝你好運。
謝謝;也祝你好運。那就,嗯,晚安了這時她把習慣性咬過的指甲舉到唇邊,不確定地咯咯笑了一聲。我是說,再見。韓德森先生。
接下來的場景在飲水器旁,華特一走近,喬‧考林斯冷靜的眼神立刻充滿憐憫。
喬,華特說。我要走了。被炒魷魚。
不!但考林斯的震驚明顯出於善意;這不算什麼意外。老天,華特,這些人到底有什麼問題?
然後佛列德‧赫姆斯插話,非常嚴肅又遺憾,明顯幸災樂禍:天啊,小子,真是太遺憾了。
華特領著兩人到電梯旁,按了下的按鈕;忽然間其他人從辦公室各個角落逼近他,僵硬的臉色帶著悲傷,手伸在前面。
非常抱歉,華特
祝好運,小子
保持聯絡好嗎,華特?
點頭微笑握手,華特說謝謝、再見、一定的;然後某台電梯的紅燈亮起伴隨叮!的機械聲,過了幾秒鐘電梯門打開,操作員說了聲下!他退進電梯裡,臉上仍然掛著固定的笑,快活地對著說話熱誠的臉孔揮手致意。電梯門緊緊關上,場景到此完美結束,電梯在沉默中下降。
下樓的路上,他臉色紅潤、眼睛明亮,充實而喜悅地站著;直到他快步走在外面的街上,他才發現自己多麼享受剛才那一刻。
震驚讓他的速度慢了下來,最後他靠在一棟大樓前面暫停了快一分鐘。他的頭皮在帽子下發麻,手指慌亂摸索著領帶的結和大衣鈕釦。他覺得被自己可憎而羞恥的行為嚇到了,這輩子從未如此的無助和害怕。
然後,他一鼓作氣繼續前進,調整帽子和下巴,腳跟用力踩在人行道上,裝出一副有急事的模樣。大白天下午在萊辛頓大道中央,過度自我分析是會讓一個人抓狂的。現在該做的就是,讓自己忙起來,開始找工作。
唯一的問題,當他又停下來環顧四周的時候,他發現他不知道自己往哪裡走。
他站在大概四十幾街左右,角落有明亮的花店和計程車,衣著體面的男女走在清新的春天空氣裡。首先他需要電話。他趕緊過街到一間藥房裡,穿越廁所肥皂、香水、番茄醬和培根的味道,走到後面牆邊的一排電話亭;他拿出電話簿翻到上面列了幾間職業介紹所電話的那一頁,他去那些地方填過申請函;然後便準備好一堆十分錢,把自己關在電話亭裡。
然而每一間介紹所說的都一樣;他現在過來也沒用,等他們打給他再說。打完電話他又把電話簿掏出來,捜尋一個熟人的電話,一個月前這人說他們辦公室可能會出現職缺。電話簿不在他的胸口內袋裡;他把手伸進外套其他口袋去找,然後又找褲子口袋,手肘撞上電話亭痛得要命,但只找到書桌裡那些舊信和半截巧克力。他咒罵了幾句把巧克力丟在地上,用腳踩了一下,彷彿那是根點燃的菸頭。電話亭裡種種費力的舉動使得他呼吸急促,他的頭暈了起來的時候,才看見電話簿就在面前,投幣箱的上面,剛才他自己放在那兒的。他撥號的手指微微發抖,開口說話時,他用另一隻手把領口從流汗的頸子拉開,他的聲音像乞丐一樣虛弱又迫切。
傑克,他說。我想說想說,不知道你有沒有之前你提過那個職缺的消息。
什麼的消息?
那個職缺。你知道,就上次你說你們辦公室
哦,那個啊。沒有,目前還沒有消息,華特。一有消息我會跟你聯絡。
好的,傑克。他把折疊門拉開,靠在貼著印花錫片的牆壁上,大口吸進灌進來的冷空氣。我只是想說你會不會忘了,他說,聲音幾乎恢復正常。抱歉打擾你。
哪會,沒關係,電話那頭精力充沛的聲音說。怎麼了,小子?你那邊情況有點麻煩嗎?
噢,沒的事,華待聽見自己這麼說,立刻慶幸自己撒了個謊。他幾乎從來不說謊,每次都訝異原來說謊這麼容易。他的聲音漸漸自信起來。沒有,我這邊很好,傑克,我只是不想你知道的,我以為你忘了還什麼的,就這樣而已。家人都好嗎?
通話結束,他想除了回家之外已經沒別的事可做。但他在門開著的電話亭裡坐了很久,伸出腳擱在藥房地板上,一直到臉上出現一抹狡詐的微笑,慢慢消失之後再轉換成正常的表情。撒謊毫不費力讓他起了個念頭,愈想愈讓他做出深刻而革命的決定。
他不跟老婆講。運氣好的話,這個月結束前他就能找到什麼差事,這段期間內,他決定這輩子第一次,把煩惱留給自己就好。今晚她問他今天過得怎麼樣,他就說:噢,還好,甚至不錯。早上他就在平常時間出門,在外面待一天,然後每天持續一直到找到工作。
他腦子裡出現振作起來這句話,電話亭裡的他讓自己振作起來,不光是果斷可以形容;他收起零錢、整理領帶、走到街上:那是一種高貴。
到正常回家時間前還有幾個小時要度過,當他發現自己正在四十二街上往西走,便決定到公共圖書館裡耗掉。他邁出大步走上寬闊石階,沒多久便安頓在閱覽室裡,檢閱《生活》雜誌去年的合訂本,在腦子裡反覆推敲他的計畫,一邊擴張一邊使其更完善。
合理而言,他知道毎日的欺瞞不會是簡單的事。必須像歹徒一樣,時刻保持警覺和狡猾。但不就是因為計畫有難度才值得去做的嗎?而且到一切都結束,他終於可以告訴她,每分每秒的折磨都有了報酬。他知道到時她會用什麼樣的眼神望著他先是空洞不可置信,然後眼裡漸漸出現他已經幾年不見的,她對他的尊敬。你的意思是你一直瞞著我?為什麼,華特?
噢,他會不經意地說,甚至聳肩,沒必要讓你擔心。
該離開圖書館的時候,他在大門口流連了一分鐘,大口吸菸,往下看著五點的車流與人流。這場景讓他特別感傷,因為五年前一個春天傍晚,他來到這裡第一次和她見面。你來圖書館的最上一層台階和我見面好嗎?當天早上她在電話裡這麼說,一直到好幾個月以後,他們已經結婚了,他才想到這真是個奇怪的會面地點。
他問起來,她笑他。當然不方便啊那就是重點。我就是想站在那裡擺個姿勢,像城堡裡的公主,要你走完全部的台階來把我帶走。
的確就是這種感覺。那天他提早十分鐘離開公司,先趕到中央車站,在地下層亮晶晶的洗手間盥洗刮鬍子;他不耐煩地等那個又矮又胖又慢的老服務員拿他的西裝去熨。付完超出他能力範圍的小費之後,他急忙往外走到四十二街,緊張又上氣不接下氣地經過鞋店和雜貨店,飛快穿越慢得令人無法忍受的行人,這些人完全不曉得他任務的急迫性。他怕遲到,還有點怕一切只是一場玩笑,她根本不會出現。然而一到第五大道他便遠遠看見她站在那裡,一個人,就在圖書館台階的最上方穿著時髦的黑外套,一個苗條而容光煥發的褐髮女孩。
於是他慢下來。信步穿越第五大道馬路,一手插在口袋裡,輕鬆、矯健、若無其事地步上台階,絕對不會有人猜到這一刻是花去多少小時的焦慮和多少天的謀略換來的。
當他差不多能確定她可以看見他的時候,他便再次抬頭看她,她笑了。那不是他第一次看見她這麼笑,卻是他第一次可以完全確定這個笑只給他一個人,喜悅讓他的心暖了起來。他不記得彼此說了什麼打招呼的話,但記得他確信兩個人沒問題,這是好的開始她閃亮的大眼睛看著他的方式,就是他希望被注視的方式。無論他說了什麼,她都覺得風趣,而她說的話,或是她說話的聲音,讓他覺得自己這輩子從來沒有這麼高壯、肩膀如此寬闊。他們轉身並肩步下台階,他攬著她的上臂把她帶走,手指背面感覺到每走一步她的胸部輕盈跳動。延展在腳下等著他們的夜晚,看似神奇地漫長也神奇地充滿承諾。
現在,單獨走下來,那一次確定的勝利給他無比力量他這輩子至少曾有一次拒絕了失敗的可能性,而且贏了。
他過馬路以後沿著四十二街的緩坡繼續往下走,其他回憶逐漸清晰了起來:那天晚上他們也是往這邊走,在巴爾的摩喝一杯,他記得在昏暗的雞尾酒吧裡她坐在他身邊的模樣,她扭著起身讓他幫她脫掉外套袖子之後再坐下,長髮一撥,然後挑撥地斜看他,一邊舉杯到嘴唇邊。過了一會兒她說:噢,我們到河邊去吧我最喜歡這時候去河邊。他們便離開飯店走到那裡去。現在他走過去,穿越第三大道的鏗鏘聲走向都鐸市大廈一個人走,大廈彷彿大了許多最後站在小欄杆旁,往下看著開在東河公路上的時髦汽車,看著遠處緩緩而流的灰色河水。就在這裡,當一艘拖船在遠處皇后區暗下來的天際線下呻吟,他第一次吻了她。現在他轉過身變了一個人,準備走回家。
走進家門迎面而來的第一樣東西,是球芽甘藍的香味。孩子們還在廚房裡吃晚餐:他聽見碗盤聲之外高頻率童音的嘟噥,然後是他老婆的聲音,疲憊的安撫。門關上的時候他聽見她說,把拔回來了,孩子們開始大喊,把拔!把拔!
他小心翼翼把帽子放在走廊櫃子上,一轉身便看見她站在廚房門口,在圍裙上擦手,對他疲憊地笑。總算有一天準時回家,她說。太好了。我還怕你今天又要加班。
不用,他說。今天不必加班。聲音在他自己耳朵裡聽起來陌生又奇怪,像經過擴大器似的,好像他在一個回音室裡說話。
你看起來真的很累,華特。看起來累垮了。
因為我走路回家的關係,大概不習慣吧。家裡怎麼樣?
哦,很好。但她看起來也很累。
兩人一起走進廚房,他覺得被潮濕的亮度包圍住。他用陰鬱的眼神看著牛奶紙盒、美奶滋罐、湯罐頭和穀片盒子,桃子排在窗台上待熟,他兩個孩子無比的脆弱和柔軟,唧唧呱呱的小臉上有幾條淡淡的馬鈴薯泥痕跡。
廁所裡狀況好一點。他花比平時更長的時間洗手準備吃晚飯。至少他在裡頭可以獨處。冷水繃緊他的臉,唯一的打擾是她老婆對大的孩子愈來愈不耐煩的說話聲:好了,安德魯‧韓德森。你不把布丁吃完,晚上就沒有故事聽。過了一會兒傳來推椅子和碗盤疊起的聲音,代表孩子們吃完晚飯了,拖著鞋子在地上走;門關上的聲音,代表他們被送回房間玩一個小時直到洗澡時間到。
華特仔細擦乾手,然後走出去到客廳沙發,拿著一本雜誌坐下,非常緩慢地深呼吸,顯示他的自制力。過了一分鐘她走進來陪他,圍裙已脫下,口紅也補過,端了一壺滿滿冰塊的雞尾酒。噢,她嘆口氣說。感謝上帝總算結束了。現在可以安靜一下。
我來拿酒,親愛的。他說完立刻跳起來。他希望自己的聲音現在聽起來會正常一點,但一發出來還是有回音室的共鳴。
不行,她命令。你坐著。你回家看起來這麼累,應該坐好讓人服侍。今天怎麼樣,華特?
噢,還好,他說,又坐下來。很好。他看著她量琴酒和苦艾酒的分量,敏捷快速地在水壺裡攪拌,調整托盤之後端著,從屋裡另一頭走過來。
好了,她說,在他身邊坐了下來。你來倒好嗎,親愛的?他在冰過的杯子倒滿酒之後,她舉起杯子說:噢,太美了。乾杯。她這歡樂的雞尾酒心情是仔細下過苦工的效果,他知道的。一如晚餐時間她對待孩子的嚴母態度;一如稍早之前她在超市直截了當的效率;以及晚一點臣服在他懷裡的溫柔。各種盤算過的心情依照秩序輪替,就是她的生活,或者說,已經成為她生活的模樣,她控制得很好。只有在極少情況,當他非常仔細看著她的臉,才看得出她因而被消耗了多少。
但喝一杯大大有幫助。一口苦澀清涼似乎讓他鎮定下來,而且手上杯子裡的酒還剩下令人安慰的分量。他又喝了一、兩口,才敢再次看著她,眼前是鼓舞人心的景象。她的笑容幾乎完全沒有壓力,沒多久兩人就像快樂的戀人那樣輕鬆地聊起來。
噢,坐下來放鬆太棒了,她說,頭輕輕往後靠著沙發椅套。想到今天是週五的晚上也太棒了。
沒錯,他說,即刻把嘴塞進飲料杯隱藏他的震驚。週五的晚上!這意味著他還要再等兩天才能開始找工作兩天時間被困在家裡,或是在公園裡處理三輪車和冰棒,沒有機會逃脫祕密帶給他的負擔。奇怪,他說。我差點忘記今天是禮拜五了。
噢,你怎麼能忘?她舒服地往沙發深處扭動。我等了一個禮拜就是等這天。幫我再倒一點,親愛的,然後我就要回去做事了。
他再幫她倒了一點,給自己倒了滿滿一杯。他的手在抖,撒出來一點點,但她似乎沒注意到,也沒注意隨著對話進行,他的回答愈來愈勉強。當她回頭忙家事在烤肉上塗油、放小孩的洗澡水、整理房間準備睡覺華特獨自坐著,讓理智陷入被琴酒搞糊塗的混亂中。只有一個念頭不斷出現,一則給自己的忠告,清晰又清涼,像不斷靠近唇邊的飲料:撐住。無論她說什麼,無論今晚或明天或後天發生什麼事,撐住就對了。撐住。
但孩子們洗澡潑水的聲音在室內流動,撐住變得愈來愈不簡單;等到他們被帶到他跟前說晚安,手上拿著泰迪熊,身上穿著乾淨睡衣,小臉閃亮,聞起來有肥皂香,撐住更是困難的一件事。之後他再也無法坐在沙發上。他跳起來開始踱步,菸一根接著一根,耳朵聽著老婆在隔壁房間抑揚頓挫的聲音讀床邊故事(你可以到草原上,或是巷子裡,但就是不能走進麥克格雷格先生的花園)
當她走出來,在背後關上孩子房間的門,看見他像個悲劇雕像站在窗口,低頭看著黑暗的庭院。怎麼回事,華特?
他裝出笑容轉過來面對她。沒事啊。他的回音室聲音說,電影攝影機再度啟動。從他緊繃的臉部特寫開始,然後跳接到她的動作,猶豫的她站在咖啡桌旁邊。
唔,她說。我再抽一支菸,然後就要去準備晚餐了。她又坐下來這回沒有靠在椅背上,因為此刻是她忙著張羅晚餐到餐桌上的心情。你身上有火柴嗎,華特?
當然有。他走向她,在口袋裡東掏西掏,彷彿有個東西他放了一整天就等著拿給她。
老天,她說。你看看這火柴,怎麼會變這樣?
這個嗎?他盯著褐色扭曲的火柴盒,彷彿那是一項犯罪證據。可能被我撕爛還什麼的,他說。緊張就有的習慣。
謝謝,她說,讓他用顫抖的手指點菸,然後開始用瞪大而嚴肅的眼神看著他。華特,出事了,對不對?
當然沒有。怎麼會出
告訴我真相。是工作嗎?還是你上禮拜擔心的事?我是說今天是不是發生什麼事,讓你覺得他們可能會克洛維爾說了什麼嗎?告訴我。她臉上的細紋好像更深了一點。她看起來嚴峻能幹,而且忽然間老了許多,甚至也不漂亮了一個時常面對緊急情況的女人準備接手。
他慢慢走開,走向屋裡另一邊的休閒椅,他的背部形狀完美說明了即將來臨的挫敗。他走到地毯邊緣停下來,好像整個人僵硬了,一個受傷的人試著撐住;然後他轉身面對她,臉上隱約出現一個憂鬱的微笑。
唔,親愛的他舉起右手去摸襯衫中間的釦子,彷彿要解開它,然後呼出一口大氣往後癱倒在椅子上,一隻腳滑到地毯上,另一隻收在椅子下。這是他一整天做過最優雅的一件事。我中槍了。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