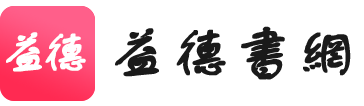一
老夫人出殯後沒幾天,就傳來一個可怕的消息:晉省東天門已被德法洋寇攻破,官兵潰敗而下,平定、盂縣已遭逃兵洗劫。日前,亂兵已入壽陽,紳民蜂擁逃離,闔縣驚惶。與壽陽比鄰的榆次也已人心惶惶,紛紛做逃難打算。
榆次緊挨太谷。彼縣一亂,接下來就該祁太平遭殃了。
三爺先得到這個消息,立馬就回來見老太爺。還沒有說幾句呢,孫北溟和林琴軒兩位大掌櫃也先後到了,危急的氣氛頓時如烏雲密佈。
可康笏南精神萎靡,似乎還未從喪婦的悲傷中脫出。他聽三人都在叫嚷時局危急,便無力地說:該怎麼應對,兩位大掌櫃去跟老三一道謀劃吧。是福是禍,都是你們的事了。我這把老骨頭留著也多餘,誰想要,就給他。
兩位大掌櫃慌忙勸慰,康笏南也不聽勸,直說:去吧,去吧,你們去謀劃吧。我聽這種紅塵亂事,心裡發煩。去吧,去吧,不敢誤了你們的大事。
康笏南既這樣說,兩位大掌櫃也不便違拗,又勸慰幾句,退了出來。
三爺忙跟了出來,將兩位引至前頭客廳,吆喝下人慇勤伺候。兩位剛落座,三爺就拱手作揖道:老夫人新喪,老太爺精神不佳,偏就遇了這危難臨頭。康家興亡,全賴兩位大掌櫃了!我初涉商務,甚不懂事,有得罪兩位的,還望多海涵。尤其孫大掌櫃,年前我有大不敬,更望見諒!
來不來三爺就這樣賠禮,大出林琴軒意料。但他沒搶先說話,想叫孫大掌櫃先接話。今日孫大掌櫃似也失去了往常的威風,見三爺先給了自己面子,也就接了話說:
三爺不要多心!誰不知三爺有俠腸義膽?所以我跟三爺說話,也就直來直去。三爺千萬不可多心!
林琴軒這才說:都是一家人,有些小小不然,快不用提它了!還是先議眼前的危局吧。
三爺就說:那就先聽孫大掌櫃的高見!
孫北溟今日所以謙和許多,是有些被這風雲突變給嚇著了。亂兵將至,遍地洗劫,他一聽這樣的傳言,先想到的就是去年京津兩號遭遇的劫難。京號雖然丟了,但戴掌櫃畢竟臨危不亂,巧為張羅,將櫃上存銀分散出去,顯出高手做派。他真沒有想到,老號竟也忽然面臨了這樣的危難!臨危不亂,似也可做到,可如何巧為張羅,卻是一點抓撓也沒有!老號存銀可不是小數目,如何能分散出去?若老號似津號那般被打劫,他這把老骨頭也成多餘的廢物了所以他慌忙跑來,實在是有些心虛膽怯的。見三爺恭請他先說,也只好說:
三爺,我哪有高見?去年至今,時局大亂,生意做不成,天成元老號存銀滯留不少。當務之急,是將老號巨銀移出秘藏!
林大掌櫃說:在太谷商界,天成元非同小可!你移巨銀出號,還不引發傾城大亂?
孫北溟說:號中存銀,當然須秘密移出。
林琴軒說:巨銀移動,如何能十分秘密的了?
孫北溟說:沒有這種本事,豈能開票號?
林琴軒說:我們茶莊可沒有這種本事。茶貨如何秘密移出,還望孫大掌櫃不吝指點呢!
孫北溟就說:庫底的那些茶貨能值多少錢?將銀子和賬本移出秘藏就得了。
林琴軒說:那東家呢?東家偌大家資又如何移出?移出後,又能匿藏何處?
孫北溟說:東家自有東家的辦法。
林琴軒說:照孫大掌櫃意思,豈不是大難將臨,各自逃生?既然如此,我們還計議什麼?各自攜銀出逃就是了!
三爺忙說:孫大掌櫃所說,也是當務之急。兵禍將來,也只能先將銀錢細軟移出匿藏,保一些,算一些。
林琴軒說:三爺!以我之見,切不可如此倉皇應對。兵亂未至,我們就領頭自亂,引發闔城大亂,這哪像康家做派?
孫北溟說:那就坐以待斃?
林琴軒說:去年隆冬,三爺南行不在時,北邊紫荊關、龍泉關也曾軍情危急。老太爺並未慌亂,邀來本邑曹培德、祁縣喬致庸,從容計議,謀得良策。計議畢,曹培德就去見了馬玉昆,探得軍中實情,心中有了數。其後,康家、曹家及喬家鎮定如常,該做生意做生意,該過年過年,全沒有慌亂避難的跡象。人心,市面,也就穩定下來。
三爺說:原來已經歷過一次驚險?
林琴軒說:可不是呢!當此之時,三爺也該先與太谷大戶緊急計議,共謀對策。這樣的兵禍,畢竟不是我們一家可抵擋。馬軍門仍駐守山西,三爺與馬軍門又有交情,何不先去拜見馬軍門?
三爺聽林琴軒這樣一說,心裡才有些主意。但他也不敢冷落孫大掌櫃,繼續恭敬地請教應對之策。末了,便說:當此危急關頭,康家全賴兩位大掌櫃了!只要兩位從容坐鎮,我們閤家上下就不會心慌意亂。
送走兩位大掌櫃,三爺就要了一匹快馬,飛身揚鞭,往北荔村曹家去了。
曹家當家的曹培德,也得到了同樣的消息,正欲去官府打聽真偽,就見康三爺火急來訪。看來,太谷局勢真是危急了。
曹培德慌忙將康三爺迎入客廳,努力鎮靜了說:三爺是稀客,好不容易光臨一回,何故這麼慌張?來救火呀?
三爺說:真比火上房還急,貴府還沒有聽說?
曹培德才說:是說東天門失守吧?
三爺說:可不是,眼看潰兵要來洗劫太谷了!
曹培德說:你家老太爺經見得多,器局也大,一向臨危不亂的。今三爺火急如此,莫非局勢真不妙了?
三爺忙問說:仁兄難道另有密報?
曹培德說:我哪來密報?這不,正要進城向官府打聽真偽呢!
三爺說:縣衙能知道什麼?我們該速去拜見馬玉昆大人!阻攔潰軍,抗衡洋人,也只有馬軍門可為。
曹培德說:我早聽說馬軍門已經接了上諭,要移師直隸鎮守。朝廷早改封馬大人為直隸提督了。此前,與馬軍門一道鎮守山西的四川提督宋慶老帥,也奉旨率川軍移師河南。
三爺說:難怪洋寇如此猖獗!守晉重師紛紛調出,難道朝廷要捨棄山西?
曹培德說:捨棄倒也不敢。山西為西安屏障,捨晉豈能保陝?調走重師,怕是以為和局將成,可以兼顧他省防務吧。
三爺說:天天都在說和局,和局又在哪?朝廷將駐晉重師移出,洋寇圍晉重兵卻不但不撤,反而趁機破關而入!朝廷如此軟弱,我看和局也難成!
曹培德說:自去年京師丟失,已是人家的手下敗將了,還能怎麼剛強?
三爺說:我看洋寇也非天兵天將。自去秋攻晉至今,多半年了,才攻破東天門。
曹培德說:你不說朝廷往山西調來多少駐軍!
三爺就說:那我們更得速見馬軍門,代三晉父老泣血挽留!在此危急之時,馬軍門萬不能走。馬師一走,山西亂局就難以逆轉了!
曹培德說:三爺與馬軍門有交情,此重任也非三爺莫屬!
三爺說:貴府是太谷首戶,仁兄豈能推諉?我願陪仁兄去見馬軍門!
曹培德就說:那好,我們就一道去求馬軍門!只是,我們有富名在外,總不能空手去見吧?不說捐助軍餉,至少也需表示一點犒勞將士的薄意吧?
三爺說:這有何難?見了馬軍門,盡可將此意說出,不日即行犒勞!
曹培德說:都像三爺這樣,自然不難。去年臘月,北邊紫荊關、龍泉關軍情危急,你家康老太爺和祁縣喬老太爺也是怕遭潰軍洗劫,憂慮至甚。我受二老委託,去見馬軍門。馬大人倒是甚為爽快,坦言無需多慮,說他與宋慶老帥即將親赴邊關,揮師禦寇。我當時甚受慰藉,便表示年關將近,祁太平商界將湊些薄禮,犒勞將士,只是年景不好,怕不成敬意。馬軍門聽了當然很高興,便發誓言:晉省絕不會失。
三爺說:仁兄所為,在情在理。
曹培德說:當時,兩位老太爺也很誇獎了幾句。張羅犒勞之資,也由二老出面。哪想,此舉竟招來許多非議!三爺也聽說了吧?
三爺說:我由南方歸來,就趕上老夫人大喪,實在無暇旁顧的。有什麼非議?真還沒有聽說。
曹培德說:最厲害的一種,是說喬家康家又想露富!
三爺說:西幫富名,早不是藏露可左右!當此危難之際,仍守財不露,豈不是要結怨惹禍?
曹培德說:誰說不是?可沒看透這一層的,真也不少。只怕露了富,招來官兵吃大戶,卻不想一味守財哭窮也將惹來大禍!你家康老太爺和喬老太爺,本想促成一次祁太平商界的緊急會商,公議一個聯保的對策。可張羅許久,響應者不多。就是公攤一些薄資,略表勞軍之意,也有許多字號不肯成全。還是你家康老太爺器量大,說人家不肯出血,也甭勉強。大不了就我們曹、喬、康三家,也能犒勞得起官兵!喬老太爺也有手段,他張揚著請匠人造了一塊犒軍匾,凡出資的都匾上刻名。
三爺問:這手段能管事嗎?淨是怕露富的,誰還願留名?
曹培德說:你猜錯了,這手段還真管用。
三爺問:是何緣故?
曹培德說:匾上無名的,怕官兵記了仇,專挑他們欺負。
三爺說:原來如此。那後來是應者如雲?
曹培德說:倒也不是。願跟我們三家一道勞軍送匾的字號,雖也不少,畢竟有限。平幫幾家大號,人家另起一股,自行勞軍。祁幫、太幫也另有幾股,自行其是。不拘幾股吧,反正在去年年關,祁太平商界是群起勞軍,把逼近家門口的洪水猛獸給安撫住了。
三爺問:那破關而來的洋寇,也給擋回去了?
曹培德說:靈邱、五台都派駐有重兵,德法洋寇也不敢貿然深入晉境。朝廷也連發急諭,命抵禦洋寇,不能失晉。不過,從龍泉關潰敗下來的一股官兵,一路潰逃,一路搶劫,直到陽曲,才被制住。距省府太原,僅一步之遙了!
三爺說:無論洋寇,無論官兵,都是我們商家的洪水猛獸!
曹培德說:抵禦這等洪水猛獸,我們也只能憑智,無以憑力。
二
康三爺與曹培德剛派出人去打聽馬玉昆的行止,太谷忽然就駐進許多官兵。一問,竟正是馬軍門所統領的兵馬。原來,馬部官兵正欲繞道潞安、澤州,出晉赴直隸,聽到東天門失守的
警報,也暫停開拔,將所統兵馬由太原以北調至徐溝、榆次、太谷、祁縣,向南一字擺開。僅太谷一地,就開來六營重兵,城關周圍駐了四個營,大鎮范村駐了兩個營。
先聽說馬部重兵進駐,三爺和曹培德還鬆了一口氣:倚仗馬軍門,祁太平局面還不至大亂吧。但稍作細想,又感蹊蹺:軍情危急之地是在榆次以東,由故關東天門直至壽陽;馬部卻不揮師東去,倒將重兵擺到榆次以南。這是何意?難道要任敵深入,在祁太平這一線關門打狗,做一決戰?
果若如此,祁太平更要遭殃了!戰事一起,還能保全什麼?
意識到這一層,三爺和曹培德更驚出了一身冷汗。幸好探知馬軍門的大帳就設在祁縣,兩人火急飛馬赴祁求見。
馬玉昆很給面子,聽說是康三爺,當下就叫了進去。
三爺和曹培德剛落座,馬玉昆就笑道:二位給嚇著了吧?
三爺忙說:馬大人的兵馬已駐紮太谷,我們還怕什麼?
曹培德也說:我們是代太谷父老,來向馬大人致意的。
馬玉昆更笑了,說:看你們的臉色吧,哪能瞞得過我?
見馬軍門這樣,三爺也不拘束了,逕直說:我們不過是平頭草民,忽遇這樣的戰禍,哪能不駭怕!東天門既有天險可倚,又有重師鎮守,竟也被洋寇攻破?
三爺話音剛落,馬軍門忽然就滿臉怒色,大聲道:
東天門豈是洋寇攻破?全是這位岑撫台拱手讓出!
三爺這才聽出,馬軍門是朝新任山西巡撫的岑春宣發怒,雖放下心來,也不便多說什麼。馬軍門似乎也全無顧忌,一味大罵岑春宣不止。
原來,岑春宣於二月由陝西巡撫調補山西巡撫後,第一要務就是與圍攻山西的德法洋軍議和。為此,他到任伊始,即新設洋務局,由張家口聘來精通英國語的沈敦和,出任洋務局督辦,主持議和事宜。
沈敦和本是浙江人,曾留洋英國,在劍橋大學研讀法政。歸國後,為兩江總督劉坤一聘用,官至吳淞開埠局總辦,並被保舉為記名出使大臣。後因吳淞炮台案遭革職,以流罪之身發落到北地東口。去夏京師陷落後,也有一隊洋寇進犯東口。因沈敦和精通英語,就被委任與洋寇交涉。經他說動,洋寇居然撤出東口!此事報到西安行在,朝廷特旨他官復原位。
岑春宣在西安當然聽說了此事,所以一到山西任上,就將這位擅長議和的沈敦和,聘請到自己麾下。
進入辛丑年,也即光緒二十七年,原東西洋八國又加比、西、荷三國,共十一國聯軍,與清廷本已就十二款和約大綱草簽畫押,除京津直隸外,洋軍也陸續從各地撤離。惟獨圍攻山西的德法軍隊,不肯後撤。德軍統帥瓦德西又是聯軍統帥,德法如此圍晉不撤,清廷也不敢大意。去年洋軍攻陷京津時,這位瓦德西還未來華,他是在秋天才趕來就任統帥的。雖出任統帥了,卻沒有多少侵華戰功,所以攻打晉省,他的勁頭挺大,想趕緊撈一些戰功以服眾。議和全權大臣李鴻章,屢屢與德法交涉,都無結果。對方公使竟以此係瓦帥軍事機密搪塞!
朝廷調集各地重兵守晉,仍不斷有危急軍情發生,太后甚感煩心。一怒之下,將錫良開缺,給岑春宣加封了頭品頂戴、兵部尚書銜,調來補任山西巡撫。所以岑春宣知道,盡快與德法洋軍議和,解去山西之圍,當是最能取悅太后的。聘來精通洋務的沈敦和,就是為成就這件事。
可僅憑精通洋務,就能退去德法重兵?想得也太天真。德法從東北兩邊圍晉,已有數月之久,尤其在邊關山野度過了一個嚴冬,豈肯聽幾句美言好話,就罷兵而去?沈敦和在東口退敵,其實靠的是重賄。竄入那裡的小股洋寇,經數日搶掠,本來已經盆盈缽滿,再得重賄,當然容易勸走。現在是大軍壓境,如何行賄?
沈敦和幾經交涉,也許之以重利,圍攻晉省東天門的德軍一直無回應,只有法軍發來一紙照會:晉省守軍全行退入山西境內,才可議和。
法軍為何提出這種要求?原來山西與直隸交界的東天門,是由故關、舊關、娘子關幾處險要關隘組成。雖有易守難攻的天險之利,可這幾處關隘都在地勢峻拔的石山巔,駐紮不了大隊兵馬,又乏水源。所以,鎮守東天門的大同總兵劉光才,就將大隊兵馬分散駐紮到東天門內外的山谷之間、近河之地。關隘之上築了重力炮位,山谷間佈滿大隊援兵和後勤糧彈,互為依託,使關防堅不可破。駐在關隘以外的營地,多屬直隸所轄的井陘地界。久踞獲鹿、井陘的德法洋軍,每每攻關,都被遍佈山谷的晉軍所阻。現在,法軍要求晉軍退入晉境,實在是要斷東天門的天險之威!
所以,馬軍門和劉總兵極力堅持:決不能答應法軍要求。井陘也不屬法土,何理命我軍撤出?
可岑春宣為推動議和,奏請西安軍機處後,竟同意劉部守軍撤回晉境。只是要求在我軍後退時,德法軍隊也同時後撤。
法軍見我肯退,就發來新照會:法軍本無意西進,現在與你方兩軍齊退,好像法方害怕你方華軍,恐被西洋他國譏笑,所以萬不能照辦。你方駐軍必須先行退出井陘,才可議和。否則,德法將合兵西進!
法軍分明是得寸進尺,越發不講理了。可岑春宣依然奏報軍機處,言明為避免給洋軍留下借口,還是同意我軍先行撤退。軍機處竟也批准。
劉總兵和馬軍門力阻不成,只好準備撤軍。東天門晉境一側,多為不宜駐兵的乾石山地,大部兵馬須退至遠離關隘的平定、盂縣城關附近。這幾乎等於將東天門拱手讓出了。
就在劉總兵被迫張羅撤兵之際,法軍五千人、德兵八千人,乘火車出京南下,緊急增援駐紮在獲鹿、井陘的德法軍力。洋寇意圖已再明顯不過:先誘逼我軍後撤,爾後集重兵破關而入!
在京的議和大臣李鴻章,得知德法增兵西進,給岑春宣發來急電,告知正就此事與德法交涉,但也難保洋軍將領為邀功貪利,在我撤兵後,破關深入,進犯晉省。望作提防,不敢大意。
可岑春宣居然表示:即便洋軍來犯,也不能再開戰釁。為早日成就議和計,我敗固貽誤,我勝亦貽誤。反正是不能與洋寇交戰!
馬玉昆言及此,早已是怒火沖天:今敵已破關,我軍不戰而潰,平定以下已是局面大亂,也未見岑撫台去赴死!
三爺大膽問了一句:即便敗局難挽,也輪不到岑大人去赴死吧?
馬玉昆冷笑一聲,說:沒人叫他赴死,是他誇了海口,要去赴死。他堅令劉總兵撤回東天門,我說劉部先行撤出容易,洋寇撲來追殺就難抵擋了。這位岑大人就慷慨許諾道:如真有此危情,宣惟有身赴敵營,與之論理。如其不聽,宣甘願繼之以死,阻其開戰!今洋寇已破關而入,一路殺掠過來,也未見岑大人身赴敵營,以死阻戰!
曹培德忽然給馬玉昆跪下,說:晉省局面既已如此危急,我等平頭草民的身家性命,祖業祖產,全繫於馬軍門一身了!今能挽狂瀾於即倒者,非馬軍門莫屬
三爺也跟著跪下,說:三晉父老都企盼馬軍門火速揮師東進,抗擊洋寇!我們西幫也願多捐軍餉,助大人抗洋
馬玉昆忙叫兩位起來,說:二位要這樣,算是錯看我了!我豈不想揮師迎敵?只是已有上諭在先,命本部移師直隸。及今也未接新旨,不能妄動。新近佈兵於徐溝至祁縣一線,屬撤出晉省的路線。今暫停開拔,即為保晉。洋寇一旦進犯至此,我部以逸待勞,當會撲而殲之!你們盡可放心,無須驚慌的。
聽馬軍門這樣說,三爺和曹培德心裡越發不安了:以逸待勞,撲而殲之,即便真如此,戰事也還是在祁太平地界。戰事起處,真不敢奢望還能保全什麼!
三爺不由感嘆一聲說:別地戰事早平息了,洋寇何以這樣與山西過不去?
曹培德也嘆道:洋人痛恨毓賢,毓賢也早革職查辦了,為何依然不肯與晉省議和?
馬玉昆笑笑,說:二位最應該知道其中緣由的。
三爺和馬玉昆茫然相視,實在莫名所以,懇請馬軍門指點。
馬玉昆說:二位真是騎驢數驢!洋寇不肯放過晉省,還不是因為貴省是塊肥肉?如你等這樣的富商富室遍地,就是洗劫也油水大呀!攻入晉省,洗劫一過,再向朝廷追加賠款。晉省既是富省,追加的賠款會少嗎?洋人不傻,他們圍晉多半年,歷盡艱辛,圖什麼?
聽馬軍門這樣一說,三爺和曹培德更是驚出一身冷汗。
三爺茫然說:洋人也知晉省之富?
馬玉昆說:洋行洋商豈能不知你們西幫底細?再說,還有跟在洋寇後面的教民呢,他們什麼不知!
曹培德就說:今幸有馬軍門鎮守晉土,也是天不亂晉吧?
馬玉昆果然昂揚地說:二位放心,有本帥兵馬在,洋寇一旦深入晉中,便成甕中之鱉矣!
馬軍門說得這樣慷慨激昂,也難釋三爺和曹培德的驚慌:看來馬軍門依然要將祁太平一帶作為抗洋的戰場。勝負不說,戰事是難免了。馬部兵馬不肯揮師東進,是有聖旨管著,憑三爺和曹培德的情面哪能說動?所以,他二人也只能極力恭維馬軍門一番,驚慌依舊,退了出來。
三
東天門守將劉光才總兵,是在三月初一將大部兵馬撤回故關、舊關的。到三月初五,德法洋軍就集結重兵,撲關而來。
此軍情急電報到西安行在的軍機處,所做處置也不過:一面電旨李鴻章,速向德法公使交涉詰責;一面命晉撫岑春宣查明詳情,及時報來。至於要不要迎敵開戰,卻是語焉不詳!朝廷上下都有一大心病:戰釁一開,攪黃了和局,如何了得?但再失晉省,西安也難保了,和局又得重議。
就在軍機處左右為難的時候,陝西道監察御使王祖同,上了一奏折,為朝廷出了一個主意:
竊自停戰議款以來,我軍遵約自守,未嘗輕動。而洋兵時出侵軼,不稍斂戢。紫荊、獲鹿先後被擾。當草約畫押後,又迫劉光才以退守,不煩一兵,坐據井陘之塞。近復闌入晉域,奪我巖關,太行天險,拱手失之,平定一帶岌岌可慮,太原全省也將有震動之勢矣。夫此退彼進,多方誤我,不能力拒,而徒恃口舌相爭,已屬萬難之舉,若並緘口捫舌,聽其侵逼,置不與較,以此求和,和安可保?
山右殷富巨商,彼實垂涎,擇肥而噬,勢有必至。現時中國利權多為外洋侵據,尚賴西商字號緩急流通。若被搜刮一空,不特坐失巨利,將各省餉源立形困敝,與大局實有關礙。且各國傚尤,殷厚之區處處肆掠,伊于胡底!愚臣以為凡開議後被擾各地,宜查估喪失確數,悉於賠款內扣除,雖得不償失,或可稍資抵制。
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王祖同這個扣減賠款的主意,當然不是高招,更不能算高尚的義舉,但軍機處卻是頗為賞識。見到王祖同奏折的當天,就代朝廷發電旨給李鴻章:
奉旨:洋兵擅逼晉境,已過故關,殊與前約不符。現聞到處滋擾,即使不任意西趨,亦應力與辯論。如仍似在京津直隸勒索銀兩,掠搶財寶,將來須在賠款內作抵,庶昭允協。欽此。
不能義正辭嚴聲明迎敵還擊,也總得說句硬話吧?扣減賠款,實在是一種恰當的說詞!不過這道電旨的弦外之音,已然要放棄晉省了。
軍機處發出這道電旨是在三月初十,其時不光是平定、壽陽、榆次,就連太原省城及祁太平一帶,也早是傳言紛紛,人心惶惶,外逃潮流幾不可遏。
三爺和曹培德見過馬玉昆,於趕回太谷前,往祁縣喬家拜見了喬致庸前輩。說起見馬軍門經過,喬老太爺說,他與祁縣幾家大戶,已拜見過馬大人了。但看喬老太爺神態,似不焦急,與平素也無多少不同。
三爺就問:馬軍門莫非給你們吃了什麼定心丸?
喬致庸一笑,反問:馬軍門也不是喬家女婿,何以會偏心我們?
曹培德就說:我們是看老太爺無事一般,有些不解。祁太平已危在旦夕,你們倒穩坐釣魚台,不是心中有數,何能如此消停?
喬致庸就問三爺:你家老爺子也驚慌失措了?
三爺說:老夫人新喪,家父還沉於傷悲,只說天塌了他也不管。
喬致庸說:這就是了,你家老太爺也未驚慌,還說我?
三爺仍不解,說:家父那能算不驚慌?我們康家真是禍不單行,老夫人新喪,又趕上這樣的兵禍,家父無力料理,我也力不能勝呀!
曹培德說:遇了這樣危難,誰能輕鬆應對?喬老太爺歷世久,富見識,多謀略,還望多指教,以共渡難關!
喬致庸說:我多活幾年,與你們能有什麼不同?既無奇兵可出,又無奇謀可施,果真潰軍來搶,洋兵來殺,也只能聽天由命了。想破了這一層,也就無須慌張。慌張也沒用呀!
三爺說:喬老太爺還是不肯直言。難道我們就坐等殺掠?
喬致庸說:朝廷擁天下重兵,尚不敵洋寇。我們無一兵一卒,怎麼抗洋?
曹培德說:那我們只有及早逃難一條路?
喬致庸說:小戶人家,一根扁擔;中常人家,幾輛馬車,就舉家逃難走了。我們怎麼逃?浩浩蕩蕩一旦上路,更成搶劫目標了!眼下出逃者雖眾,也多為小戶及中常人家。以我之見,我們大戶切不可妄動。在祁太平,我們商家大戶一動,必然傾城都動。到了那一步,敵未至,先自亂,便不可收拾了。
三爺說:老太爺還是叫我們坐以待斃?
喬致庸說:以老漢愚見,現任晉撫岑春宣,諒他也不敢將晉省拱手讓給洋寇。朝廷給他加封頭品頂戴、兵部尚書,難道就是叫他來開關迎寇?
曹培德說:聽馬軍門說,岑撫台是寧死不開戰釁的,所以才有東天門之失。
三爺也說:洋寇已破關多日,晉省盡陷於敵手,只是遲早的事!
喬致庸說:馬軍門的話,我們不能不聽。可你們就沒有聽出來?馬對岑頗多不屑!我們去拜見時,馬軍門大罵岑:恃才妄為,不聽吾言,逕自撤東天門守軍,惹此禍亂。我問馬軍門:何不率部出壽陽退敵?馬軍門竟說:只待洋寇入晉陷省城,擄去岑大人後,請看本帥克城救彼,易如反掌耳!聽聽,馬軍門按兵不動,原來是要岑春宣的好看!給你們說這種話沒有?
三爺說:倒未這麼明說。
曹培德說:兩位鬥法,遭殃的只是我們!
喬致庸說:當時我問馬軍門:晉省表裡山河,進來不易,出去也難;攻破東天門的德法洋寇,真敢孤軍深入進來?
三爺忙問:馬軍門如何回答?
喬致庸說:他說洋夷用兵,別一種路數,魯莽深入也難說。敝老漢不懂兵法軍事,但叫我看,洋軍也不至如此魯莽。即便深入晉境,也須步步為營,留一條能進能出的後路。洋軍大本營在京津,京津至太原千里之遙,又跨太行天險,一路佔據,需調多少兵力?所以,我們不必太慌張,自亂陣腳。
三爺說:我們一路撤兵降敵,人家也無須多少兵力!
曹培德也說:洋軍未到,潰敗下來的官軍,就似洪水猛獸了!
喬致庸說:近日收我們省號賈繼英送來的急報,說他剛拜見過岑撫台,確知岑大人已派出重兵開赴壽陽,彈壓潰軍搶掠。
三爺說:這還算一條好消息。
曹培德說:潰軍彈壓下了,洋寇跟著進來!
喬致庸說:洋寇真來了,也只能破財保根基吧?我聽賈繼英說,洋務局的沈敦和在東口議和,也無非是敢破財!送洋寇銀數萬兩,羊千頭,馬千匹,牛百頭,駝百峰,狐裘百餘襲,羊裘千餘件。
三爺驚問:我們亦如此,那不是受辱降寇了?
曹培德也驚歎說:去年以來,我們西幫已破財太甚!
喬致庸說:除了破財,惟有破命。去年的拳民就是走破命一途,結果如何?如今朝廷都受降議和了,我們還能怎樣?
三爺和曹培德想了想,覺得真到了那一步,也只能如此了。朝廷官軍無力拒敵,一心議和,商家不受此辱又能如何!只是,破了財,就能保住根基嗎?真也不敢深想。
如何阻擋眼下的逃難風潮,三人計議半天,也無良策,僅止於聯絡大戶大商號,儘量穩住,不敢妄動。
在趕回太谷的路上,三爺和曹培德更看到舉家出逃者,絡繹不絕。此種風潮再蔓延幾日,局面真將不可收拾!所以,兩人一邊策馬趕路,一邊議定:到太谷後,三爺去見武界領袖車二師傅,請鏢局派精幹把式,速潛往東天門打探真情;曹培德即往縣衙見官,申明商家願與官方一道共謀安民之策。
三爺趕到貫家堡車二師傅府上時,李昌有等一干形意拳高手都在。
三爺向各位武師一一作揖行過禮,就將見馬玉昆的情形略說了說。眾人就爭著問:洋寇到底已攻到哪了?是否已攻破壽陽?
三爺說:東路軍情,馬軍門不肯詳告,只說洋寇魯莽深入,攻陷太原,都是可能的。
眾人也問:洋寇將至,馬部大軍為何按兵不動?三爺只說:馬軍門還未接到揮師迎敵的上諭。
李昌有便說:我們正議論呢,看官軍架勢,一準不想與洋寇交手!平頭草民紛紛出逃,就是看官軍指靠不上。可我等是習武之人,難道也似一般民眾,棄鄉逃亡?
車二師傅也說:去年夏天,義和拳民蜂起殺洋教,我們形意拳弟兄多未參與。洋教在太谷,結怨並不多。幾位教士被殺,也有些過分。今洋軍攻打過來,只是查辦教案,倒也罷了。如濫殺無辜,強掠姦淫,我們形意拳兄弟可就不能再坐視不理!
三爺驚慌問道:車師傅你們也要起拳會?
李昌有說:我們不會像義和拳,見洋人就殺。武界尊先禮後兵。洋軍來時,我們潛於暗處,靜觀不動。彼不行惡,我們也不難為他;但凡有惡行,當記清人頭,再暗中尋一個機會,嚴懲不貸!如係大隊作惡,當先刺殺其軍中長官。
三爺說:這與拳會有何不同?
李昌有說:拳會是烏合之眾,徒有聲勢,並不厲害。我們不會挑旗招搖。洋軍在明處,我們在暗處,無形無跡,只叫洋寇知道形意拳的厲害!
武師們的大義,是叫三爺感動。可這與拳會畢竟類似,一旦給官府知道,哪會被允許?官府怯於與洋寇交戰,可剿滅拳會不會手軟。拳師暗殺洋寇,也必然要擴大戰釁,祁太平更得陷於水火之中。但三爺知道,他出面阻武師們的義舉,也不會收效的。所以,他也沒有多說,只是照原來目的,請求車、李二位師傅,派出高手,趕赴東路平定、盂縣一帶,打探洋寇犯晉的真實軍情。
車二師傅說:已經派出探子了,有探報傳回,一定相告。三爺有新消息,也望及時通氣。三爺連聲應承,又隨武師們的議論附和幾句,就匆匆告辭出來。
眼看天色將晚,三爺卻無心回康莊去。多少焦慮壓在心頭,回到家中又能與誰論說?以往遇大事,都是老太爺扛著,你想多插嘴也難。現在,老太爺像塌了架,連如此危急的戰禍都不理睬。這真似忽然泰山壓頂,三爺很有些扛不住了。他不由又想到邱泰基。自己身邊還是少一個足智多謀的人,邱掌櫃遠在西安,那位能幹的京號戴掌櫃,也遠在上海。
天成元老號的孫大掌櫃,那當然不能指望。
現在,只有去見茶莊的林大掌櫃。能不能謀出良策,先不論;只是說說心頭想說的話,眼下也惟有林大掌櫃了。
於是,三爺吩咐跟隨的一個小僕,回康莊送訊,自己便策馬向城裡奔去。
林琴軒見少東家摸黑趕來,還以為出了什麼事。慌忙問時,才聽三爺說:跑騰了一天,還沒有吃頓可口的茶飯。我是跟你們討吃來了。灶房還沒封火吧?
林琴軒放下心來,說:三爺想吃什麼,儘管吩咐!灶火還不便宜?
三爺說:不拘什麼吧,清淡些,快些,就成。
林琴軒說:總得燙壺酒吧?
三爺就說:不喝了。今日太乏累,能喝出什麼滋味?不喝了。
林大掌櫃說:喝口酒,才解乏!難得三爺來一趟,我陪三爺喝一壺。
三爺說:既受林大掌櫃抬舉,那就燙壺花彫吧。
三爺哪能喝花彫!我這裡有幾罈汾州杏花村老酒,林大掌櫃轉臉朝身後一夥友說:快吩咐灶房,先炒幾道時鮮的菜,燙壺燒酒,麻利些!
三爺剛洗漱畢,酒菜已陸續端來。與林大掌櫃這樣燈下對酌,真還不多,可三爺喝著老酒,品出的卻儘是苦味。他將見馬軍門、喬致庸以及車二師傅的經過,簡略說了說,感嘆跑騰一天,未遇一件如意事!
林琴軒忙說:三爺也不必太心焦了,大局如此,亦不是誰能左右得了。岑撫台既已派重兵彈壓壽陽潰兵,這畢竟還是好消息。局面不亂,才可從容對敵。
三爺說:洋寇眼看攻殺過來,如何能不亂!
林琴軒說:叫我看,洋寇還不至輕易攻殺過來。
三爺問:何以見得?
林琴軒說:只要馬軍門統領重兵駐守晉省腹地不動,我看洋寇也不敢貿然進來。岑撫台想成就議和,只怕也會不惜多讓利權,換取洋寇退兵。任洋寇攻殺進來,佔去省府,那還叫議和嗎?丟了晉省,西安危急,朝廷如何能饒得了他?太后賞他一個頭品頂戴來山西,也不是叫他來喪土降敵吧?
三爺說:但洋寇也不是那麼好哄吧?既千辛萬苦攻破東天門,哪能輕易罷兵?聽馬軍門說,洋夷用兵,是另外一路,很難說的。
林琴軒說:我們跟洋夷也做過許多生意了,他們可傻不到哪兒!晉省地形,他們不會不顧及。深入進來,就不怕斷其後路,成甕中之鱉?所以叫我看,大局還是和多戰少。洋人攻入晉境,無非多加些賠款,也就成了和局。
三爺說:真如林大掌櫃所說,那還讓人放心些。
林琴軒說:喬老太爺說得很對,我們大戶大號千萬不能妄動!我們一動,誰還敢不動?到那一步,局面可就不好收拾了!
三爺說:眼下大戶大號倒是都沒動,可外逃潮流不還是日甚一日?照這樣下去,過不了幾天,大戶大號也要慌!
林琴軒說:大字號表面未動,暗底裡誰家敢靜坐不動?我跟伙友們也在底下張羅呢!
三爺說:所以我說,不用幾天,不拘洋寇攻來沒攻來,祁太平局面必將大亂!百姓傾城蜂擁逃難,駐守的官軍豈肯閒著?他們早視祁太平是肥肉。一想今後幾日情景,就叫人心驚肉跳!
林琴軒說:聽三爺說,曹培德正與官衙共議安民之策?
三爺說:正是。就怕謀不到良策!岑撫台頂著兵部尚書的頭銜,尚不敵洋人,縣令出面說話,誰又肯聽?
林琴軒說:三爺,我倒有一安民之策!
三爺忙問:大掌櫃有什麼良策,快說!
林琴軒說:目前局面是人心惶惶,官府貼佈告,不會有人信;可稍有傳言,都信!所以,設法散佈一些能安定人心的傳言,說不定還管用。
散佈些安民的流言?
這也算略施小計吧。
三爺立馬振作起來:林大掌櫃獻出的這個小謀略,可是今天最叫他動心的了!在馬軍門、喬老太爺及車二師傅那裡,都未曾聽到類似的奇謀。自家這位大掌櫃,真還不能小看。
林大掌櫃,這個計謀甚好!只是,何種流言才能阻擋鄉民外逃?
林琴軒說:叫我看,不在編出什麼傳言,而在誰編、編誰!
三爺忙問:我沒明白,大掌櫃說的什麼意思?
林琴軒倒反問:三爺你說,現在鄉民還敢相信誰?
三爺竟一時不該如何回答:也真是
林琴軒笑了,說:傳言官軍能抵擋住洋寇,最沒人信!說我們大字號得了密報,議和將成,洋寇將退,只怕市間也是半信半疑。現在惟有一家,鄉民尚敬重不疑。
誰家?
即三爺剛拜見過的形意拳武師們。
車二師傅他們?
對。車二師傅、昌有師傅他們,武藝高強,德行也好,在江湖中的名望誰不知道?傳言他們已有對敵之策,鄉民也許會駐足觀望,暫緩出逃的。但凡有一點指望,誰願背井離鄉!
三爺點頭說:車二師傅他們出面,勢必應者如雲。只是,如此一來,會不會將他們的形意拳,傳說成義和團似的拳會,惹官府疑心?
林琴軒忽然就擊掌說:三爺,你和曹培德就不會居中說合,叫縣衙將形意拳編成鄉勇?新編鄉勇,不說抗洋,只說對付潰兵流匪。如能說成,再勸武師們率眾來城裡公開操練演武。
其時,我們商界前往慰勞,縣衙也去檢閱。有了此種氣象,不用多置一詞,鄉民也會傳言紛紛,駐足觀望的。
三爺一聽,也擊掌說:林大掌櫃,明日一早,我就往縣衙獻上你的計謀!事到如今,我看縣衙也別無良策了。
至此,三爺才來了酒興。對林大掌櫃,他也更刮目相看了:林大掌櫃的才具,當在孫大掌櫃之上吧。
四
隔日,在城裡東寺旁的空場上,真聚集了二百來名鄉勇,在形意拳武師的統率下,持械操練。間或,爆出幾聲震天動地的喝叫,傳往四處。聞聲趕來觀看的民眾,也就越聚越多。
在場邊,車二師傅、昌有師傅幾位武林領袖,康家習武的康二爺、曹家習武的曹潤堂等幾位大戶鄉紳,以及縣衙的幾位官吏,正在神色凝重地議論時局軍事。聲音很高,語意明瞭,並不避諱圍在身後傾聽的一般民眾。
他們的話題,多集中在如何對付潰兵流匪上,言語間,對將至的兵匪甚是不屑,又議論了一些擒拿兵匪的計謀。這叫擠在一邊旁聽的鄉民,聽得很順心,很過癮。
這中間,也對洋寇來犯,稍有議論。武師、鄉紳們都煞有介事主張:對洋寇須智取,不能硬碰硬。洋寇到時,可殺豬宰羊先迎進來,再擺酒席大宴之;席上只備燒酒,務必悉數灌醉。
等洋寇醉死過去,可往洋槍槍管、洋炮炮筒內澆入尿湯;一過尿湯,洋槍洋炮就失靈了這類降敵方法,更令鄉民聽得興味高漲。
後來,知縣大人駕到,檢閱了鄉勇操練,聽了武師、鄉紳的退敵之論,誇獎一番。縣令剛走,幾家大商號又來慰勞。
第二天,在北寺附近也有一隊鄉勇在操練,情形與東寺相差不多。
於是,官衙、武林、商界聯手平匪禦敵的種種消息,就由民眾口口相傳,迅速傳遍全縣城鄉。民心果然稍定,外逃風潮開始減緩。
這幾天,三爺也一直住在城裡的天盛川老號,各方奔忙,一直未回康莊。見局面有了好轉,正想痛快喝一回燒酒,就有僕傭來傳老太爺的話:趕緊回來!
匆匆趕到家,就聽四爺說:這幾天已將年少的男主和年輕的女眷,送出去避難了。六爺及各門的小少爺,三娘、四娘及汝梅以下的小姐們,都走了。
三爺一聽,就有些急:他四處勸說別的大戶不可妄動,自己家眷倒紛紛出逃了。他問是誰的主張,四爺說當然是奉老太爺之命。不過,都在夜間潛出,又都化了裝,沒多少人知道。
三爺能說什麼,只在心裡說:夜間出逃的並不少,怎麼能秘密得了!
康笏南聽到東天門失守,洋寇攻入晉境,官家潰兵將至的消息,心頭有些像遭了雷擊:這是上天對他的報應嗎?
因為杜氏的喪事剛剛辦完,就傳來了這樣可怕的消息。以他的老到,當然知道這消息意味著什麼:康家的祖產祖業面臨著滅頂之災!太谷真遭一次兵禍,康家的老宅、商號必然成為被洗劫的重頭目標,康家幾代人、歷幾百年所創的家業,就將毀於一旦
這樣的兵禍,不光在他一生的經歷中,就是在祖上的經歷中似乎也不曾有過吧。咸豐年間鬧太平天國,危急時大清失了半壁江山,都以為戰禍將至。外埠字號撤了回來,老宅、老號的家產、商資也做了匿藏準備。結果,是虛驚一場。那次戰禍,起於南方,亂在南方,這邊慌是慌,畢竟離得遠,逃難也能從容準備的。
這一次,兵禍就在家門口,說來就來了,天意就是不叫你逃脫吧?
去年朝廷有塌天之禍,危情不斷,但於太谷祖業終究也只是有驚無險。眼看議和成了定局,怎麼兵禍忽然又降臨到家門口?
這分明是上天的報應!
如果不送走杜氏,就不會有這樣的兵禍吧?
分明是報應
康笏南面對突臨的兵禍,就一直擺不脫這樣的思路。越這樣想,他就越感到心靈驚悸,精神也就垮了下來。他把應對危機的重擔,那樣草率地撂給了三爺,實在也是不知所措了。
這在康笏南,可是前所未有的!
不論在家族內部,還是在康家外面的商業王國,康笏南一直都是君臨一切的。他畏懼過什麼!家事商事,就像三爺所深知的:別人就是想插手也很難,他哪裡會把主事權輕易丟給你?
康笏南給失寵的老夫人這樣辦喪事,也不是第一次。以前,他可沒有這樣驚悸過。他老謀深算,事情辦得一點紕漏都沒有。日後就是鬧幾天鬼,他也根本不在乎。但這一次似乎有些不同。治喪期間,好像人人都動了真情,為杜氏悲傷,卻不大理會他,彷彿他們已經看穿了一切。所以在未知兵禍臨頭前,他已有些心神不定,恍惚莫名。
老夏和老亭一再說:沒有一點紕漏,誰也不會知道真相。他不相信這兩個人,還能相信誰?也許他自己衰老了吧?人一老,心腸就軟了,疑心也多了?
或者,他真應該受一次報應?
時局一天比一天可怕,康笏南也一天比一天感到軟弱。他自認逃不過報應,也只好預備捨身來承受,但祖業還得留給後輩去張羅。所以,他不敢再拖延,決定向三爺交代後事。
對老三,他依然不夠滿意,可還能再託靠誰?
三爺見到老太爺,大感驚駭:就這麼兩天,老太爺好像忽然老了多少歲!精神萎靡,舉止發癡,人也像整個兒縮小了他當然不知道父親內心的驚悸,依然以為父親是丟不下新逝的杜老夫人。
父親對杜氏有這一份深情,也難得了。
三爺一到,康老太爺就把所有僕傭打發開,氣氛異常。
父親大人,你得多保重!三爺先說。
康笏南無力地說:我也活夠了,不用你們多操心。外間局勢如何?
三爺忙說:局面已有好轉。近日商界、武林與官衙聯手,已止住外逃風潮,民心稍定。
潰軍和跟在後頭的洋寇呢,也止住了?
聽說岑撫台已派出重兵,到壽陽彈壓潰軍。退守樂平的大同總兵劉光才,也出來除剿亂兵。
洋寇呢?洋寇攻到哪了?
還得不到洋寇的準信,只聽說岑撫台在極力議和。
既已攻破東天門,人家能跟你議和?叫我看,洋寇不攻下太原,決不言和。這一兵禍,那是逃不過了。
父親大人,依我看,戰與和,還各佔一半。馬軍門的重兵,尚在晉中腹地駐守著,洋寇也不敢輕易深入吧?
東天門也有重兵鎮守,還不是說丟就丟了?不用多說了,這場劫難是天意,別想逃過去。
父親大人,既如此危急,那你也出去躲躲吧。由我與二哥、四弟留守,盡力應對就是了。
老三,今日叫你來,就是向你交代後事的
三爺一聽這話,慌忙跪下說:父親大人,時局真還未到那一步!即便大局崩盤,太谷淪陷,我們也會伺候父親平安出走的。
康笏南停了停,說:我哪也不去了。這場劫難非我不能承擔,此為天意。我已到這把年紀,本也該死了,但康家不能亡。所以,該出去避難的是你們。我留下來,誰想要,就給他這條老命。你起來吧,這是天意。
三爺不肯起來,說:父親大人,這不是將我們置於不孝之地了?
康笏南說:這是天意,你們救不了我的。你快起來,我給你看一樣東西。
說時,康笏南從袖中摸出一頁信箋,遞了過去。三爺也只好起來接住。展開看時,上面只寫著寥寥幾行字,又都是儀門假山、偏門隱壁之類。什麼意思,看不出來。
康笏南低聲說:老三,這是我們康家德新堂的九處隱秘銀窖。你要用心記住!這九處銀窖,也沒有暗設許多機關,只是選的地界出人意料就是了。總共藏了多少銀錠,我說不清。只能告訴你,這些銀兩足夠支撐康家遍佈天下的生意。
三爺這才意識到了這頁薄箋的份量,默數了一下,是九處。三爺從小就知道家資巨富,但到底有多富,直到他接手料理商事,也全然不知。現在,家資就全在這頁薄紙上了,只是銀窖所在的確太出人意料,幾乎都在明處
康笏南問:記住了沒有?
三爺忙說:記住了。
康笏南便說:那你就點一根取燈,燒了它。
三爺聽說是這個意思,忙又看了一遍,才點了取燈,燒著了這頁薄紙。
康笏南說:這九處銀窖,你永遠只能記在心上,不能寫在紙上。這是向你交代的第一樣。
三爺忙答應:我記住了。
第二樣,這些銀兩永不能作為家產,由你們兄弟平分。這是祖上傳下來、一輩一輩積攢起來的商資老底。康家大富,全賴此活水源頭,永不能將它分家析產!你能應承嗎?
永記父親囑托!
此為不能違背的祖訓。
知道了,當永遵祖訓。
第三樣,這份商資在我手裡沒少一兩,多了一倍。我一輩子都守一個規矩:不拘商號賺回多少錢,都是分一半存進這銀窖中,另一半作家中花銷;賺不回錢,就不花銷。這規矩,我不想傳給你,但這份老家底在你手裡不能虧損太多。
我謹守父親的規矩,賺二花一,不賺不花。
世事日艱,尤其當今朝廷太無能,我不敢寄厚望於你。我傾此一生,所增一倍商資,總夠你虧損了吧?祖上所遺老本,你們未損,我也就滿意了。
父親交到我手上的,我亦會不損一兩,傳給後人!
老三,你有此志,當然甚好。但遇此無能朝廷,你也得往壞處想。所以,我交代你的第四樣,就是也不能太心疼這老家底:商事上該賠則賠。祖上存下這一份商資,既為將生意做大,也為生意做敗時能賠得起。西幫生意能做大,就憑這一手:賠得起,再大的虧累也能賠得起!不怕生意做敗,就怕賠不起。賠不起,誰還再理你?大敗大賠而從容不窘,那是比大順大賺還能驚世傳名。
因大敗大賠而驚世揚名?
因你賠得起,人家才更願意跟你做生意!當然,不賠而成大事最好。西幫事業歷練至今,也漸入佳境,少有大閃失了。只是,遇了這太無能的朝廷,似也劫數難逃。去歲以來,損失了多少!眼前大劫,由我抵命就是。但以後亂世,就得由你們張羅了。生意上遭賠累不用怕,這些商資老底還不夠你們賠嗎?就是把我所增的那一倍賠盡,也要賠一個驚天動地了。先賠一個驚天動地,再賺一個驚天動地,那就可入佳境了。怕的是你們捨不得賠,希圖死守了這一份巨資,吃香喝辣,坐享其成!
父親放心,我們不會如此不肖!
那我就交代清了。後世如何,全在你們了。
父親大人,局面還並不似那麼無可挽回!
你不用多說。眼下還有些小事,你替我檢點一下吧。你們兄弟各門逃難走前,不可將珍寶細軟藏匿得太乾淨,宜多遺留一些。無論潰兵,還是洋寇,人家衝殺進來,沒有劫到多少值錢的東西,怒火上來,誰知道往哪發洩?明處的那兩個日常使喚的銀窖,也要多留些銀兩,尤其要遺留些千兩大錠。世間都知道西幫愛鑄千兩銀錠,劫者不搜尋出幾錠來,哪能過得了癮?孫大掌櫃那裡,你也過問一下,天成元櫃上也不可將存銀全數密運出去,總得留下像樣的幾筆,供人家搶劫吧?什麼都劫不到,饒不了你。聽明白了吧?
聽明白了。
檢點過這些事,你跟老四也避難去吧。你大哥、二哥他們,能勸走,也趕緊叫他們走。這裡的老家底,我給你們守著。但願我捨了老命,能保全了家底。
父親大人不走,我們也不會走的!
你們不走,是想叫康家敗亡絕根嗎?
五
三爺雖不敢太違拗老太爺,但他哪裡會走?本來與曹培德就有約,不能妄動;現在老太爺又將康家未來託付給他,更不能臨危逃走了。
他去勸大哥、二哥,他們也都不想走。大哥還是閉目靜坐,不理外間世界。大娘說,我們也年紀不小了,還怕什麼?二爺日夜跟形意拳武師們守在一起,忙著操練鄉勇,計議降敵之策,正過癮呢,哪會走?
四爺當然也不肯走,反倒勸三爺走。
勸不走,就先不走吧。反正外間的逃難風潮也減緩了。
可就在老太爺交代後事不久,外間局面又忽然生變:馬玉昆派駐太谷的幾營官軍,突然開拔而去。也並非進軍東路,去迎擊洋寇,卻是移師南去了!由榆次開過來的馬部駐軍,也跟著往南移師。
馬軍門統領的重兵,要撤離山西!
三爺聽到這個消息,又驚出了一身冷汗:朝廷真要放棄晉省了?說不定是再次中了洋寇議和的詭計!東天門之失,就是中了洋寇的詭計。說好了敵我齊退,結果是我退敵進。官軍前腳撤出關防,洋寇後腳就撲關而來。現在,你想叫洋寇退出晉境,人家又故伎重演。馬軍門的官軍一退,洋寇洋兵必定乘虛而來!
三爺不敢怠慢,立馬去尋曹培德,商量對策。
曹培德倒不像三爺那樣著急,說已經派人往祁縣打聽消息去了。叫他看,馬玉昆重兵撤出山西,說不定還是一種好兆。若軍情危急,西安軍機處能允許馬軍門撤走?三爺依然疑心:一定是岑春宣急於議和,將馬軍門逼走了。馬部重兵一撤,山西必成洋寇天下!
曹培德也沒太堅持,只說:洋寇真來了,我們也只能殺豬宰羊迎接吧?
三爺說:我們殺豬宰羊倒不怕,就怕人家不吃這一套!
曹培德說:我看,再邀祁太平幾家大戶,速往省城拜見一回岑撫台。見過岑大人,是和是戰,和是如何和,戰又如何戰,也就清楚了。
三爺說:這倒是早該走的一步棋。岑春宣移任晉省撫台後,祁太平商界還未賀拜過。只是,今日的岑春宣好見不好見?
曹培德問:你是說見面的賀禮嗎?
三爺說:可不是呢!去年,岑春宣只是兩宮逃難時的前路糧台,寫一張千兩銀票,孝敬上去,就很給我們面子了。現在的岑春宣已今非昔比,該如何孝敬,誰能吃準?
曹培德說:叫我看,只要我們不覺寒酸,也就成了。岑春宣吧,又見過多少銀錢!喬家的大德恆在太原不是有位能幹的小掌櫃嗎?該備多重的禮,托他張羅就是了。該斟酌的,是再邀哪幾家?
三爺說:不拘邀誰家,也得請喬家老太爺出面吧?你我都太年輕。
曹培德說:喬老太爺年長,人望也高,只是喬家並非祁縣首戶。喬老太爺出面,平幫會不會響應,就難說了。我看,請祁縣渠家出面,比喬家相宜。渠家是祁幫首戶,又有幾家與平幫合股的字號。渠家出面,三幫都會響應。
三爺說:請渠家出面,那也得叫喬家去請。
曹培德說:那我們就再跑一趟喬家?
三爺說:跑喬家,我一人去吧。仁兄還得聯絡武林、官衙,繼續操練鄉勇。官軍撤了,鄉勇再一散,民心更得浮動。
曹培德就說:那也好。只是辛苦三爺了。
二位還未計議完,曹家派出打聽消息的武師,已飛馬趕回來了。帶回的消息是:馬玉昆兵馬已全軍開拔,由祁縣白圭入子洪口,經潞安、澤州,出山西繞道河南,開赴直隸。傳說朝廷有聖旨:和局將成,各國洋軍要撤離,所以命馬部官軍趕赴直隸,準備重新鎮守京畿地界。所以,說走就走了。
和局將成,洋寇要撤離?真要是這樣,那當然是好消息;可看眼前情形,誰又敢相信?
三爺反正不敢相信,疑心是軍機處怕開戰釁,使了手段,將主戰的馬玉昆調出了山西。曹培德也不大敢相信,只是以為:若調走馬玉昆,能使三晉免於戰事,也成。但三爺說:
就怕將山西拱手讓給洋人,人家也不領情,該搶還是搶,該殺還是殺!
曹培德就說:馬部兵馬已走,就看洋寇動靜了。眼下,攻入晉境的洋寇到底推進到哪了?日前聽知縣老爺說,平定、盂縣兩地縣令竟棄城逃亡,岑撫台已發急諜嚴飭各縣,再有棄城者,殺無赦。所以知縣老爺說:既不叫棄城逃難,那就打開城門,殺豬宰羊迎洋寇吧。
三爺說:朝廷棄京逃難走了,洋寇還不是將京城洗劫一過!殺豬宰羊迎接,洋人就會客氣?我不敢相信。車二師傅派出的探子,也傳回消息說,壽陽、榆次縣衙已會集商紳大戶,令預備迎接洋寇的禮品貨物。鄉人聽說了,更惶恐出逃。馬玉昆這一走,祁太平一帶的逃難風潮會不會再起?
二位計議半天,覺得當務之急還是如何安定民心,對付洋寇,賀拜岑春宣倒可緩一緩的。商界的巴結,哪能左右了岑春宣?他該議和還不是照樣議和!
既不往祁縣遊說喬家渠家,三爺就趕去見車二師傅。
近日車二師傅一直住在城裡的鏢局。一見三爺來,就問:三爺,來得這麼快?
三爺不明白是問什麼,就說:車師傅,快什麼?
車二師傅說:康二爺才走,說去請你,轉眼你就到了,還不快?
三爺說:我剛從北荔村曹家來,並未見家兄。有急事?
車二師傅說:那三爺來得正好,正有新探報傳來!
三爺忙問:洋寇來犯?
車二師傅一笑,說:算是喜訊吧,不用那樣慌。
喜訊?
能算喜訊。
的確能算喜訊:攻入晉境的德法洋軍,已經撤回直隸的井陘、獲鹿了,並未能大舉西進。
原來,三月初一,鎮守東天門的劉光才總兵被迫撤兵時,怕故關、舊關及娘子關的炮台成孤立之勢,不能持久,就設了一計:密令這三處關防的守將,明裡也做撤退假象,暗裡則將陣地潛藏隱蔽,備足糧彈存水。這樣佯退實不退,為的是不招敵方圍困;洋寇若大意撲關,又能出其不意,迎頭痛擊。
果然,德法洋軍派過來刺探軍情的華人教民,聽信傳言中了計,把關防炮台守軍也撤退的情報,帶回去了。
初四夜半,法軍撲故關,德軍朝娘子關,分兵兩路西進,企圖越關入晉。因為已經相信是空關,大隊兵馬徑直往前開時,無論德軍法軍,都沒有攻關打算。哪能想到,大軍都擠到關下了,忽然就遭到居高臨下的重炮轟擊!德法兩軍遭遇都一樣,死傷慘重,驚慌後撤。不同的是,德軍從娘子關後退時,又走錯了路,與從故關敗退下來的法軍,迎面相撞。初四後半夜,正是黑得伸手不見五指的時候,驚慌撤退的雙方未及細辨,就以為遇到了清軍的埋伏,於是倉皇開戰。等明白過來,又傷亡不少。洋寇連夜退回井陘,據說將跟隨他們的教民,殺了不少。教民謊報軍情,洋人以為是有意的。
洋寇吃了這樣大的虧,哪能甘心?初五、初六兩日,連續發重兵,圍攻故關、娘子關及南北嶂幾處關防。雙方傷亡都夠慘重,娘子關也一度失守,但洋寇終未能長驅入晉。此後相持數日,也時有戰事,但已波瀾不驚。到三月十三,德法洋軍都退回獲鹿,連戰死的屍骸也運走了,怕是要放棄攻晉吧。
三爺聽了,當然鬆了一口氣,說:洋寇息戰,當然是喜訊。只是,東天門關防雖危急,並未盡失,潰軍之亂又從何說起?
車二師傅說:那是盂縣一幫歹徒趁危興風作浪。娘子關失守後,洋寇並未敢單道深入。可附近一個鄉勇練長,叫潘錫三,他聽說關防失守,就勾結一幫不良官兵,四處散佈洋寇已破關殺來,引發民亂。他們就趁亂肆意搶掠。此亂一起,那就像風地裡放了一把野火,誰知道會燒到哪!不用說一般鄉民了,盂縣、平定的縣令就先嚇得棄城逃跑了。
三爺說:劉總兵機智阻敵在前,拚死守關在後,怎麼也不見張揚?只聽說潰軍將殺掠過來,還以為就是劉部兵馬呢。
車二師傅說:德法撲關伊始,劉總兵就急報岑撫台,岑只讓勸止,不許開戰。劉大人只好急奏西安軍機處,岑撫台知道後,反責備劉大人謊報軍情。這種情形,誰還敢為之張揚?派去探聽消息的武友,很費了周折,才得知實情。
三爺又能說什麼?雖然知道了兵禍暫緩,可以鬆口氣了,但還是更記起父親交代過的那句話:當今朝廷太無能,凡事得往壞處想!
其實,德法肯退兵,到底還是因為岑春宣答應了由晉省額外支付一筆巨額賠款。這就正如林大掌櫃所預料:破財議和。
六
兵禍暫緩之後,康家逃難出去的,也陸續回來。老太爺的精神分明也好轉了。但三爺卻輕鬆不下來:老太爺秘密向他交代了康家的老底,他算是正式挑起重擔了吧。
所以,三爺終日在外奔波,不敢偷閒。但一件棘手的事,卻令他想躲也躲不開:兵禍才緩,票莊的孫大掌櫃就提出要告老退位。
這次兵禍雖然有驚無險,孫大掌櫃的表現卻令人失望,一味慌張,沒有主意,哪還像個西幫的大掌櫃?或許孫大掌櫃也真是老邁了。只是,他是老太爺依靠了幾十年的領東掌櫃,三爺哪敢擅自撤換?尤其有去年冬天的那次齟齬,三爺更不能就此事說話了。他剛主事,就叫領東老掌櫃退位,別人不罵他器量太小才怪!
再說,更換領東大掌櫃,畢竟是件大事。要換,也得待天時地利人和俱備之際,再張羅吧?眼前時局,哪容得辦這種事!三爺心裡已有了自己中意的大掌櫃,可他連一點口風都沒敢透出。
因此,孫大掌櫃一跟他提起這事,三爺就極力勸慰,直說這種時候康家哪能離得開你老人家呀!天成元遇了這樣的大難,除了你老,誰能統領著跳過這道坎?你老要退位,天成元也只好關門歇業啦。總之,揀好聽的說吧。
可孫大掌櫃好像鐵了心要退位,你說得再好聽,他也不吃這一套。
這是怎麼了?孫大掌櫃是被這場兵禍嚇著了,還是另有用意?以他的老辣,覺察出老太爺已經交代了後事,三爺正式繼位,所以不想伺候新主了?
老太爺交代後事那是何等秘密,三爺哪敢向世人洩漏半分?他連三娘都沒告知一字!孫大掌櫃是從他的言行舉止上覺察出來了?近日他是太張揚了,還是太愁楚了?自家就那樣沉不住氣?
三爺躲也躲不過,勸也勸不下,就對孫大掌櫃說:這麼大的事,跟我說也沒用。大掌櫃想告老退位,去跟我們老太爺說。我自家出趟遠門,還得老太爺允許呢,這麼大的事,跟我說頂什麼事?
孫北溟卻說:我還不知道跟你家老太爺說?說過多少回了,都不頂事!前年,津號出了事,我就跟他說,該叫我引咎退位了吧?他不答應,怕傷了天成元信譽。去年京津莊口被毀,生意大亂,應付如此非常局面,我更是力不能勝了。可你家老太爺依舊不許退位,說留下這麼一個亂局,沒人願接!這不是不講理嗎?這麼個亂局,也不是我孫某一人弄成,豈能訛住我不放?現在,洋人退了,議和將成,亂局也快到頭了,還不允許老身退位?
三爺只是說:這是我們老太爺器重你,離不開你。
孫北溟說:他是成心治我!三爺,我求你了。孫某一輩子為你們康家效勞,功勞苦勞都不說了,看在我老邁將朽、來日無多的分上,也該放了我吧?入土之前,我總得喘息幾天吧?你們家老太爺,他是恨不得我累死在櫃上才高興!三爺,你替我說句話,替我在老太爺跟前求求情,成不成?
三爺現在畢竟老練多了,孫大掌櫃說成了這樣,他也沒敢應承什麼,依舊說:孫大掌櫃,在我們家老太爺跟前,我說話哪有你老頂事?我替你求幾句情,有什麼難的?只怕我一多嘴,老太爺反而不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