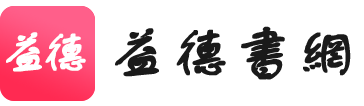一
三月初八這個日子,六爺最不能忘記了:去年因洋人陷京,朝廷將耽誤了的恩科鄉試,推延至今年的此日開考。
朝廷發此聖旨的時候,還正在山西北路逃難呢,就以為今年三月能雨過天晴?三月是到了,朝廷卻依然在西安避難。議和受盡屈辱,還是遲遲議不下來。德法洋軍倒攻破晉省東天門,殺了進來。不用說,恩科比試又給攪了。
六爺聽到兵禍將至的消息,最先想到的,就是當今皇上的命數,實在是太不濟了。三旬是而立之年。皇上三旬壽辰開的這個恩科,居然就這樣凶禍連綿!看來尊貴如皇上,竟也有命苦的;該著的劫難,逃也逃不脫。逢了這樣的皇上,你也只能自認命苦吧。
本來,聽說發生拳亂的州縣將禁考五年,六爺已經斷了念想,自認倒霉,自認命苦。想不開時,偷偷吸幾口料麵,飄飄揚揚,也就飛離苦海了。沒想到,年後從西安傳來消息,說禁考條款只是應付洋人,朝廷已有變通之策:禁考州縣的生員,可往別地借闈參考。山西屬禁考省份,鄉試將移往陝西借闈。京師也在禁考之列,會試將移在河南開封府借闈。
借闈科考,這是誰想出的好主意?
六爺趕緊振作起來,頭一樣,就是決定戒煙,再不能吸料麵了。吸大煙後,他算知道煙癮是怎麼回事了。進入考場,一旦煙癮發作,哪還能做錦繡文章?堂皇森嚴的考棚裡,大概不會允許帶入煙槍料面。
只是,戒煙哪那麼容易!煙癮來了,不吸兩口,人整個兒就沒了靈魂,除了想吸兩口,就剩下一樣:想死。
何老爺,你這不是害了我了?
何舉人當然沒有料到朝廷還有借闈科考這一手。但國運衰敗如此,忍辱借闈吧,就能選取到賢良了?朝廷無能,賢良入仕又能如何?所以,對六爺的責難,何老爺倒也不在乎。染上大煙嗜好,赴考是有些關礙,可六爺你若棄儒入商,那就什麼也不耽誤。這種話明著說,六爺當然不愛聽。
何老爺只是勸慰六爺,說戒煙不能太著急。你這才吸了幾天,煙癮遠未深入骨髓,戒是能戒了,只是不能著急。戒煙也似治病,病去如抽絲。
六爺聽了這話更著急:我倒想悠著勁兒戒煙,可朝廷的考期能悠著勁兒等你?三月初八,轉眼就到了,我不著急成嗎?
當時是正月,離三月真不遠了。
何舉人笑了笑說:就因為三月初八不遠,才無須著急。
六爺以為何老爺是成心氣他,就說:著急也沒用,反正來不及戒了?何老爺是不是有什麼妙法,能將煙具料麵夾帶進考棚?
何老爺說:六爺,到三月初八若能如期開考,咱們真還不愁將煙槍煙土夾帶進去。煙槍可製成筆型,煙土又不佔地方,塞哪吧不便宜?
六爺說:何老爺當年就這麼帶的?
那時本掌櫃正春風得意,抽什麼大煙!我染上煙癮,也跟六爺相仿,全因為斷了錦繡前程。中舉後,京號副幫做不成了,還能做甚?只好抽大煙吧。
何老爺你又來了!你不叫我著急,難道真要抽足了大煙,再作考卷?
六爺,我勸你不必著急,是因為到三月初八,肯定開不了考!這一屆恩科鄉試,保準還得推延。
何老爺又得了什麼消息?
有消息,沒消息,一準就是推延了。轉眼三月就到了,什麼動靜還沒有。議和還沒有議下來,談何借闈?
六爺想想,雖覺得何老爺推斷得有些道理,但依舊必須戒煙:不論考期推延到何時吧,總是有望參加的。
所以在正月二月,六爺算是把自家折騰慘了。煙癮發作時,牆上也撞過,地下也滾過,頭髮也薅過,可惜自虐得再狠心,終於還是免不了吸兩口拉倒。一直到杜老夫人重病時,六爺的戒煙才算見了效。
老夫人忽然重病不起,使六爺受到一種莫名的震動。震驚中,竟常常忘了煙癮。尤其在探望過老夫人後,好幾天鬱悶難消:這幾天就一點煙癮也沒有。
二月十七,老夫人真就撒手西去。從這一天起,一直到三月初七老夫人出殯,三七二十一天中,六爺居然沒發過一次煙癮!除了繁忙的祭奠、守靈、待客,他心裡也是壓了真悲痛。杜老夫人的死,自然叫他想起了生母的死。但在心底令他悵然若失的,還有另一層:他是剛剛看懂了這位後母,怎麼說死就死了?他剛剛看懂了什麼是女人,什麼是女人的天生麗質,什麼是女人的優雅開通,什麼又是女人的鬱鬱寡歡剛剛看懂女人的這許多迷人處,竟會集於後母一身,她就忽然死了。
她剛剛現出真身,忽然就死了!
在這種無法釋化的悲傷中,六爺徹底忘記了大煙土。因為他願意享受這一份悲傷,再濃厚,再沉重,也不想逃脫。
出了三月初七,六爺才忽然想起三月初八是個什麼日子。他的煙癮已去,延期的鄉試倒如何老爺所料,仍沒有如期到來。時局也未進一步緩和,反而又吃緊了。東天門失守,兵禍將至,傳來的都不是好消息。
沒過幾天,六爺跟了何老爺,趁夜色濃重,逃往山中避難去了。
那是一個叫白壁的小山莊,住戶不多,但莊子周圍的山林卻望不到邊。林中青松居多,一抹蒼翠。六爺還是頭一次見到這樣廣袤雄渾的山林,稀罕得不得了。尤其在夜間起風時,林濤呼嘯,地動山搖,六爺被驚醒後那是既駭怕,又入迷:似近又遠的林濤,分明渲染著一種神秘與深邃,令你不知置身何處。
何老爺對此卻興致全無。他一味勸說六爺,與其在這種山野藏著,還不如去趟西安。眼下朝廷駐鑾西安,那裡才最適宜避難。西安離太谷也不遠!
去西安避難?何老爺真是愛做奇想。六爺也未多理會,只是說:西安我可不想去,只想在這幽靜的山莊多住幾天。這麼壯觀的林子,何老爺多經見了?
六爺,你真是氣魄不大。與朝廷避難一城,你就不想經見經見?
與朝廷同避一城?
你既鐵了心要入仕途,也該趕緊到西安看看。
看什麼?
看朝廷呀!朝廷整個兒都搬到西安了,又是臨時駐鑾,最易看得清楚!京中朝廷隱於禁宮,與俗市似海相隔。棄都西安,哪有許多禁地供朝廷隱藏?所以朝廷真容,現在是最易看清的時候!
何老爺,現在是朝廷最倒運的時候。你是叫我去看朝廷的敗像嗎?
朝廷的敗象,你輕易也見不著吧?
攛掇我去看敗象,是什麼用意,我明白!
我有什麼用意?
還不是想敗壞我科舉入仕的興致!
六爺,這回你可冤枉本老爺了。我攛掇你去西安,僅有一個用意:沾六爺的光,陪了一道去趟西安。朝廷駐鑾西安,敗也罷,盛也罷,畢竟值得去看看。漢唐之後,西安就沒有朝廷了,這也算千載難逢吧!
何老爺這樣一說,六爺倒是相信他了。只是,跟何老爺這樣一個瘋人出遊西安,能有什麼趣味?所以,他也沒有鬆口:
西安真值得去,眼下也去不成吧?我們正逃難呢,哪有心思出遊?再說,老夫人初喪,也不宜丟下老太爺,出門遠行。
六爺,到無災無難時,朝廷還會在西安嗎?
何老爺仍極力攛掇,六爺終也沒有應承。但趁朝廷駐鑾之際,去遊一趟西安,倒真引起六爺的興致。反正考期又推延了,大煙癮也已去除,正可以出遊。日後借闈開考,也在西安,早去一步,說不定還能搶到幾分吉利吧。
只是,無論如何也不想跟何老爺同去。有他在側,太掃興。但除了何老爺,又能與誰結伴出遊?
六爺也沒有多想,就有一個人跳了出來,浮現在眼前:這個人竟是孫二小姐,那位已跟他訂親的年少女子。
他這也是突發奇想吧,竟然想跟未婚妻結伴出遊?那時代,訂婚的雙方在過門成親以前,不用說結伴出遊,就是私下會面,也是犯忌的。而自訂親後,六爺實在也很少想起這位孫小姐。在老夫人安排下,他暗中相看過對方,看不出有什麼毛病,卻也未叫人心跳難忘。
但在老夫人重病不起後,他開始時時想到孫小姐了:她是老夫人為他物色到的女子。那一次在華清池後門,也許並沒有很看清。又是冬天,包裹得太嚴實。不是很出色的,老夫人能看得上嗎?六爺已生出強烈的慾望:能再見一次孫小姐就好了。可除了老夫人,誰又會替他張羅這種事?重病不起的老夫人,再不會跟他一起搗這種鬼了。那次搗鬼,真使他感到溫暖異常。
只要一想,六爺就感傷不已。
老夫人病故之後,六爺就更想念這位孫小姐了:她是老夫人留給他的女人。記得她也是很美貌的,也是天足,也愛洗浴,也應該很開通吧。她也會不拘於規矩,悄然出點格,搗一次鬼嗎?
在為老夫人治喪期間,六爺就止不住常常這樣想。那時他幻想的,是與孫小姐一道,為老夫人守一夜靈。在長明燈下,面對了老夫人那幅音容依舊的遺像,只有他們二位,再沒有別人當然,那也只能幻想。沒人替他張羅這種事。
現在,提到出遊西安,六爺不由得又想到孫小姐。與孫小姐一道出遊,那是更不容易張羅的出格事。但他幻想一次,誰又能管得著!
孫小姐是天足,出遊很方便。她也開通,不會畏懼見人。她甚至可以女扮男裝,也扮成一位趕考的儒生,那他們更可以相攜了暢遊西安。她扮成儒生,會太英俊吧。
這樣的幻想,使逃難中的六爺想得很入迷。有時候,為了躲開何老爺的絮叨,他就只帶了小僕,偷偷鑽進村外的松林。林子深處幽靜神秘,更宜生發幻想吧。
二
從白壁逃難回來,時局已大為緩和了,鄉試卻沒有任何消息。何老爺就繼續攛掇:到西安走一趟,什麼消息探聽不到?
剛經歷了老夫人新喪和外出避難,六爺感到窩在家中也實在鬱悶難耐。於是,真就跟老太爺請示了:聽說將在西安借闈科考,所以想早些去西安看看。趁朝廷駐鑾西安,去了,也能開開眼界吧。
老太爺居然問:這是何老爺的主意吧?
六爺一聽就明白了:這個何老爺,倒先在老太爺跟前嚷嚷過了!大概是未獲贊同,才又攛掇他出面。於是說:是我想去,不干何老爺的事。
沒想到,老太爺竟痛快地說:是你自己的主意,那更好!老六,你早該去西安看看了。朝廷落難時候是種什麼氣象,你早該去看看了!這也是千載難逢啊,西安又離得近,不去真可惜了。想去,就趕緊去吧!
老太爺說的話,也居然和何老爺一模一樣。是老太爺聽信了何老爺的怪論,還是何老爺本來就暗承了老太爺的意旨?不論怎樣吧,六爺的興致大減。他們攆他到西安,不過是為叫他親見朝廷的敗象,以放棄科舉入仕。早知這樣,他才不上當呢。現在也不好反悔了,只好答應盡早動身。
老太爺叮囑:到西安就住到天成元櫃上,多聽邱掌櫃的。邱掌櫃手眼通天,什麼都知道。
他們的用意更清楚了。六爺嘴上答應下來,心裡卻想:他才不想聽掌櫃們唸生意經,只想遊玩。再說,人在外,還不知會怎麼著呢。
去西安已無阻礙,但結伴同行的,果然指派了何老爺。六爺先興味索然了一陣,轉念一想,倒也覺著無妨:何老爺興趣在商事,到了西安準就一頭扎進鋪子,與邱掌櫃論商議政去了。
六爺盡可獨自遊玩的,只怕比在家中還要自由得多。
既如此,六爺的那個奇想又跳出來了:能邀了孫家小姐一道遊西安,那該是種什麼滋味?
若在以往,六爺才不會作此種非禮的出格之想,現在可不同了。這兩年歷盡大變故,不斷令人喪氣損志,什麼仁義禮信,他也不大在乎了。再加上杜老夫人在他心底喚醒的青春意識,已經再按捺不下。所以他反倒渴望出格!
簡直沒有多想,六爺就奮筆給孫家小姐寫下一信。信中說老夫人的仙逝,叫他痛不欲生,困在家中更是處處睹物傷情。近日,他已獲准出遊西安,一面散心,一面還可瞻仰朝廷氣象云云。只在末尾提了一筆,汝敬仰先老夫人,似大有維新氣韻,定也不憚出遊。想已遊過西安吧,可指點幾處名勝否?
信寫好,如何投遞?
六爺就想到了初見孫小姐的地界:城裡的華清池後門。孫小姐常去洗浴,那應是傳信的好地界。他叫來心腹小僕桂兒,吩咐其到華清池後門守候,設法將信件送給孫家小姐。行事要秘密,又要機靈。
桂兒應命去了,當日就跑回來稟報:信已交到了。
六爺忙問:交給了誰?
桂兒說:當然是交給了孫家小姐跟前的人。
接了嗎?
一聽是六爺的信,哪敢不接!
說什麼沒有?
孫小姐還沒從浴池出來呢,一個下人,她能說什麼?只說一定轉呈。
給孫小姐寫信本是一時衝動,打發桂兒走後,六爺才有些後怕了。太魯莽了吧,孫小姐是不是那麼開通,還兩說呢!人家不吃這一套,翻臉責怪起來,豈不麻煩了?當時就想,桂兒此去撲了空就好了,他後悔還來得及。孫小姐不會天天去洗浴,哪會那麼巧,初去就撞到?
老天爺,真還撞著了!
既已出手,結果如何,也只好聽天由命吧。想是這麼想,心裡可是大不踏實。六爺畢竟是自小習儒的本分人,又是初涉男女交往,當然踏實不了。
他囑咐桂兒,多往華清池跑跑,看孫小姐有什麼回話。
誰料,還沒等桂兒往城裡跑呢,孫家倒派人來了。
那是送出信後第二天,六爺催桂兒往城裡跑一趟,桂兒不願去,說去也是白跑,人家哪能天天去洗浴!六爺也不好再催,心裡七上八下的,坐也坐不住,動又不想動。就在這當口,管家老夏領著一個生人進來,說孫家差人來了,要面見六爺。
六爺一聽就有些慌,只以為真出了麻煩,忙對老夏說:叫底下人引他進來就得了,哪用老夏你親自張羅?
老夏笑笑,說:孫家來的人,哪敢怠慢!
六爺極力裝出常態,說:不過是個跑腿的,老夏你也不用太操心,有什麼事,叫他待會兒跟我說吧。你要不忙,先坐下喝口茶?
不了,六爺你快招呼人家吧,有吩咐的,叫桂兒來告我。
老夏走了,再看孫家差來的這個下人,也平平靜靜,六爺這才放心些了。便問:孫家誰派你來的?
那人低聲說:我們家小姐。
他們家小姐?
派你來何事?
送一道信,面呈六爺。說時,從懷中摸出一封信札,呈了上來。
六爺接住,努力不動聲色,說:就這事?
就這事。六爺親手接了,我也能回去交代了。
六爺就吩咐桂兒送孫家差人出去。兩人一走,趕緊抽出信來看:老天爺,她怎麼跟自己想像的一模一樣!信中說,接了傳來的私函,驚喜萬分,不敢信以為真;杜老夫人仙逝後,思君更切;出遊外埠名勝,正是她的夙願;與夫君相攜出遊,她已做過這樣的夢了;今遊西安,實在是正其時也;願與夫君同行,乞勿相棄;為避世人耳目,她可女扮男裝
這豈止是開通,簡直是滿紙烈焰!
這樣的信函,竟大模大樣派人徑直送上門來!
孫小姐的開通程度,雖然叫六爺大受衝擊,可他還是像抽了料麵一樣,忽然精神大振。
女扮男裝的孫小姐會是什麼樣子?更風流俊雅,還是更大膽?
眼看著自己的胡思亂想即將成真,六爺恨不得立馬就能啟程赴陝。急沖沖去跟何老爺商量行期,這老先生,卻正臥在炕榻上。一問,才知是染了風寒,大感不適,渾身上下像被抽了筋了,棉花一團軟。
這叫什麼事兒!平日也不見你害病,到了這種要命的關節上,害得什麼病?既然想害病,何老爺你就踏踏實實病著吧,我也不催逼了,只好先行一步。赴陝一路,辛苦萬狀,等踏實養好病,你再趕來西安也耽誤不了啥。
這也許還是天意,特別將何老爺早早支開,省得他礙眼礙事?
六爺就極力勸說道:何老爺,上了年紀了,貴體當緊。先踏實養你的病,就是天大的事也不用多操心。學生也該長些出息了,去趟西安哪還非用老師領著?就是跑口外吧,也該學生獨自去歷練。自古以來,遠路趕考的生員,也未見有為師的陪伴吧?何老爺你從容養病,學生就先行一步,在西安恭候老師隨後駕到。
何老爺一聽可急了,翻身滾下病榻,直挺挺站定,說:六爺,我什麼病也沒得!剛才,不過是戲言,嚇唬你呢。即便明日動身,我這裡也便宜。
六爺看何老爺的情形,卻分明一臉病容,雖努力挺著,身子還是分明在抖。
他忙扶持何老爺躺下,可老先生死活不肯挪動,直說:沒病,沒病,什麼時候啟程都便宜!
老先生不是又犯了瘋癲吧?
糾纏了半天,六爺才明白:何老爺實在是怕丟失了這次出行外埠的機會!自從頂了舉人老爺這個倒運的功名,脫離京號,還未再外出過,更不用說大碼頭了。此回赴西安,無論如何得成全了他!不過是偶感風寒,無關痛癢的。六爺,你可千萬不能將此小恙,說給老太爺知道,切切,切切。
一旦給老太爺知道,何老爺就去不成西安了?這倒也是擺脫這位瘋爺的一步棋。不過看著他那副可憐相,六爺實在有些不忍心。畢竟是老師呀!
沒辦法,只好等他幾天。
六爺答應了等,何老爺只是不相信,還是糾纏著說:千萬不能丟下他,千萬不能叫別人知道他病了。不能說給老太爺,更不能說給老夏!老夏對他一向不安好心
六爺忍不住真生了氣,丟了一句話:信不過我,你就自個兒去西安!也不管何老爺如何起急,逕自走了。
孫小姐帶給六爺的那一份激情,叫何老爺這樣一攪,倒變成了幾分無名火。回來冷靜了一陣,才想起該給孫小姐傳一聲回話過去。人家一團烈焰,你倒只顧了與這位瘋老爺生氣!
六爺展箋寫回信時,只覺自己也成了一團烈焰,奮筆疾書下去,什麼顧忌都丟到一邊了。
不久,收到孫小姐回信,依然滿紙激情。
這樣來來去去,倒也顧不上生什麼氣了。五天後,六爺先啟程上路。以他的願望,那當然是想與孫家同行!與她結伴,這一路長旅將會是何等滋味?他想像不出。但孫小姐說,在本鄉地界畢竟不便太出格,還是先分頭赴陝吧。言外之意,到了西安,才可無所顧忌?於是約定了六爺先行,孫小姐隨後再啟程。
六爺啟程時,自然將何老爺帶上了。他說小恙已大愈,誰知道呢?
其時已到四月中旬,天氣正往熱裡走。由太谷奔西安,又是一直南下。天氣一天比一天熱,沿途地界也是一處比一處熱,兩熱加一堆,趕路不輕鬆。
六爺心裡還裝著一熱:孫小姐投來的那一團烈焰。被這熱焰鼓舞著,他倒也顧不得旅程之累了。只是這位何老爺,一路不停地念叨自家當年如何不懼千里跋涉,又說前年老太爺南巡時正是大熱天氣,我們受這點兒熱哪叫熱?彷彿別人都是怕熱怕累,軟綿不堪,只他有當年練就的英雄氣概。
可剛走了五六天,到達洪洞,何老爺就先病倒了。這回是患時疾,下痢不止,人又成了棉花一團軟。
六爺也只好在這洪洞停下來,尋請醫先為何老爺診視抓藥。心裡剛要生氣,忽然一轉念,暗暗叫了一聲好:在這地界多等幾天,不就把孫小姐等來了?
他儘量顯得不動聲色,安慰何老爺不要著急上火,止痢當緊,大家也走乏了,正可乘機喘息幾天。暗中呢,打發了桂兒留意探聽孫家人馬的動靜。
洪洞倒也有幾處可遊玩的名勝,除了盡人皆知的大槐樹,霍山廣勝寺更是值得一遊的一座古寺。可六爺他哪有這份心思!
等了四五天,何老爺的時疾已漸癒,桂兒卻什麼消息也沒打探回來。
你這小猴鬼!是沒有用功探聽吧?六爺等得心煩意亂:錯過四五天了,孫家還不動身?
桂兒卻不含糊,說:洪洞有多大呢?像模像樣的客棧,又有幾家?我早打點妥了,孫家人馬一到,準給我們送信來!除非他們不在洪洞這地界打尖。
六爺忙問:不在洪洞打尖,也行?
不在洪洞打尖,除非孫家人馬是日夜兼程往西安趕。他們哪能叫孫小姐受這種罪?
孫小姐要日夜兼程,底下人也擋不住吧?
孫小姐會這樣趕趁?
我們也走得太慢了!
桂兒不過是隨口這樣一說,六爺聽了竟當了真,不敢再耽誤,立馬催攆啟程趕路。陷入情網的公子小爺們,大概都這樣,敏感躁動,又容易輕信。只是,六爺還不大意識到自己已深陷情網:他什麼也顧不上想了。這一路就想一件事,早一天到西安,見著女扮男裝的孫小姐。
三
到西安一進天成元的鋪面,何老爺的精神就大不一樣了,長旅勞頓簡直一掃而空,就連吸幾口鴉片的念想也退後了。
這些年,他最大的念想,就在這外埠的字號裡頭!
西號的程老幫和邱泰基,已知六爺一行要來陝,沒料到隨行的竟然還有何老爺:老號來信提也沒提。不過邱泰基對何老爺的光臨,還是有些喜出望外。他知道這位當年的京號副幫那是有真本事的,以前就很仰慕,可惜未在一起共過事。現在忽然相遇西安,他就未敢怠慢,恭敬程度不在六爺之下。
實在說,六爺此時來陝,邱泰基是憂多喜少。他先想到的,就是前年五爺五娘在天津出的意外。今年時局比前年更不堪,兵荒馬亂的,哪是出遊的年頭!連尋家像樣的客棧也不容易,去年冬天給三爺賃到的那種僻靜的小院,已難尋覓。西安成了臨時國都,聚來的官場權貴越來越多,好宅院還不夠他們搶呢。
邱泰基極力勸六爺和何老爺,受些委屈,就住在自家字號裡,不夠排場吧,伙友們倒也能盡心伺候。哪知,六爺說什麼也不在櫃上住!住下等客棧,車馬大店,都成,就是不想在櫃上住。
邱泰基請何老爺勸一勸,何老爺也不勸,便做主說:六爺自小習儒,不想沾商字的邊兒,就不用強求了。正好,本老爺是不想在外頭住,就由我代六爺領你們的情,住在櫃上。兩位掌櫃,也不用客氣,由我們各得其所罷。
邱泰基趕緊將何老爺拉出賬房,悄聲說出了自己的擔憂。
何老爺依然用決斷的口氣說:多慮,多慮!朝廷在西安呢,滿街都是富貴人,哪能輪到綁我們的票?
邱泰基說:官場權貴不敢惹,正好欺負我們商家!
何老爺依然口氣不變:邱掌櫃,你聽我的沒錯!有朝廷在呢,誰那麼憨,跑朝廷眼皮底下綁票?京城的行市,我清楚!
何老爺,西安不比京師。眼下西安是什麼局面?天下正亂呢!
現在西安就是京都,聽我的沒錯!
說什麼,何老爺也聽不進去,邱泰基也只好不勸了。趕緊叫程老幫張羅酒席,給二位接風。他呢,親自跑出去給六爺尋覓客棧。
跑了幾處,都不滿意,就想到了響九霄。受西太后垂眷不厭,響九霄在西安越發紅得發紫。官場求他走門子的,已是絡繹不絕,這麼一點小事,也值得求人家?邱泰基卻是有另一層想法:借響九霄幾間房子住,圖的是無人敢欺負。這比僱用鏢局高手還要保險。在西安響九霄是通天人物,誰敢惹他?
邱泰基親自上門,響九霄還真給面子,一口就應承下來了。邱泰基也說得直率:想借郭老闆的威風,為少東家圖個吉利。畢竟是伶人出身,見邱泰基這位大票號的老幫也低頭求他,心裡還是夠滿足。以前,是他這樣求邱掌櫃!
借到的自然是一處排場的院子。邱泰基就勸說何老爺也住過去,哪想,何老爺也來了個死活不去!不過,何老爺倒說得明白:他離開字號多年了,想念得很,給他金鑾殿也不稀罕,只貪戀咱這字號。
話說成這樣了,還能強求嗎?
安頓了六爺,何老爺就纏著他問朝廷動向、西號生意。邱泰基也正想有個能說話的自家人,謀劃謀劃許多當緊的事務。西號的程老幫倒是不壓制他,但見識才具畢竟差了許多,說什麼,都是一味贊成,難以與之深謀。何老爺雖離職多年,但畢竟是有器局、富才幹的老手,總能有來有往的議論些事。
何老爺先急著打探的,當然是時局:邱掌櫃,朝廷議和到底議成了沒有?我們來陝前,山西還彷彿危在旦夕,滿世界風傳洋人打進東天門了,咱祁太平一帶也蜂擁逃難。我和六爺還逃進南山躲避了十來天。跟著,忽然又風平浪靜了。何以起落如此?太谷市間有種傳說:洋人在東天門中了咱官兵的埋伏,死傷慘重,敗退走了。朝廷的官兵要真這樣厲害,京城還至於丟了?
邱泰基說:現今時局平緩下來,那是和局已經議定。洋軍圍攻山西,不過是逼朝廷多寫些賠款罷了,也不是真想攻進去。
和局已議定了?賠了洋人多少?
聽說賠款數額加到四萬萬五千萬兩,洋人算是滿意了,答應從直隸京津撤出聯軍,請朝廷迴鑾。
四萬萬五千萬?何老爺做過多年的京號副幫,他明白這是一個什麼數額!乾嘉盛世那種年頭,大清舉國的歲入也不過三四千萬兩銀子。其後,國勢轉頹,外禍內亂不斷,國庫支絀成了常事,釐金、新稅、納捐,出了不少斂錢的新招數,但如今戶部的歲入也不過是四萬萬五千的一個零頭!
聽說就是這個數,少了,洋人不撤軍。人家佔了京師,不出大價錢,你能贖回來?朝廷沒本事,也只能這樣破財免災吧。
破財,你也得有財可破!邱掌櫃,我們是做銀錢生意的,戶部每歲能入多少銀子,大清國庫總共能有多少存底,如今闔天下又能有多少銀子,大概也有個估摸。如今朝廷的歲入,記到戶部賬面上的,也就七八千萬吧,末了能收兌上來的,只怕一半也不到。就按賬面數額計,四萬萬五千萬,這是大清五六年的歲入!依現在的行市,就是把朝廷賣五六回,只怕也兌不出這麼多銀子!
誰說不是?甲午戰敗,賠東洋日本國的兩萬萬,已把朝廷賠塌了,至今還該著西洋四國的重債,國庫它哪能有存底?就是存點日用款項,這次丟了京城,也一兩沒帶出來。按說,朝廷背了債,也犯不著我們這些草民替它發愁。可天下銀錢都給洋人刮走,不用說國勢衰敗,民生凋敝,就是市面忽然少了銀錢流動,我們也難做金融生意了!
朝廷它哪知道發愁?這四萬萬五千萬洋債,無非是分攤給各省,各省再分攤給州縣,嚴令限期上繳罷了。
攤到州縣,州縣也無非向民間搜刮吧。可近年民間災禍頻仍,大旱加戰亂,本來就過不了日子了,再將這滔天數額壓下去,就不怕激起民變?聽說這次也是效仿甲午賠款,將賠款先變成洋債,再付本加息,分若干年還清。
老天爺,四萬萬五千萬變成洋債,就限二十年還清吧,只是利滾利,又是一個滔天數額了!洋人的銀錢生意眼,真也毒辣得很!
聽說這四萬萬五千萬賠款,議定分三十九年還清,年息定到四厘!本息折合下來,總共是九萬萬八千萬兩!
老天爺,九萬萬八千萬?等這筆賠款還清,大清國只怕再無銀兩在市面流通了!
聽說軍機大臣榮祿也驚呼道:外族如此佔盡我財力,中國將成為不能行動的癆病鬼了!但他是大軍機,弄成這樣,好像與他無關?
賣身契,賣身契,這是朝廷寫下的賣身契!這樣的朝廷,六爺還一心想投身效忠,憨不憨?
何老爺,我早看明白了,無論西洋東洋,不只是船堅炮利,人家那些高官大將,爵相統帥,一個個都是好的生意人!洋人可不輕商。哪次欺負我們,不是先以重兵惡戰給你一個下馬威,接下來就布了生意迷陣,慢慢算計你!你看甲午賠款,東洋人海戰得了手,叫你賠軍火,算來算去竟算出一個二萬萬的滔天大數!他東洋鬼子的艦船槍炮,難道是金鑄銀造的?算出這樣一個滔天大數來,為的就是叫你大清還不起。你還不起,西洋四國就趁勢插進來了:
我們可以借錢給你。借錢能白借嗎?西洋人寫的利息,更狠!看看,東洋人的二萬萬一兩不少得,西洋人倒平白多得了一筆巨額利息!這次庚子賠款更絕,算出一個四萬萬已經夠出奇了,又給人家寫了那麼高的年息,滾動下來賠成了九萬萬八千萬!這麼有利可圖,洋人欺負我們還不欺負出癮頭來?叫我看,朝廷養的那班王公大臣,武的不會打仗,文的不會算賬,不受人家欺負還等什麼!
邱掌櫃,你把這種話多給六爺說說!老太爺打發六爺來西安,也是想叫他見識見識朝廷的無能,丟了科考入仕的幻想。這位六爺,既聰慧,又有心志,就是不想沾商字的邊兒,憨不憨?
我說幾句還不容易?就怕六爺不愛聽。
在西安轉幾天,親眼見見京師官場的稀鬆落魄樣,我看他就愛聽了。
何老爺,你去轉兩天,也就明白了,聚到西安的這幫京中權貴,才不顯稀鬆落魄呢!
不稀鬆落魄,難道還滋潤光鮮?
反正一個個收成都不差。
在西安是避難,哪來收成?
何老爺,你還做了多年京號掌櫃呢,其中巧妙,想吧,想不出來?
可西安畢竟不比京師,能有多少油水?
朝廷一道接一道發上諭,各地的京餉米餉也陸續解到。可因為是逃難,京中支錢的規矩都無須遵守了,尋一個應急變通的名兒,還不是想怎麼著,就能怎麼著?再者,臨時屈居西安,門戶洞開,出外搜刮也方便得很。
你這一點撥,我就清楚了。生疏了,生疏了,畢竟離京太久了!
人年輕時練就的本事,輕易丟不了的。何老爺,櫃上正有件事,想請你指點。
邱掌櫃不用客氣!
這和局一定,朝廷也該迴鑾了。隨扈的那班權貴,逃出京時孤身一個,別無長物,現在要返京了,可是輜重壓身,不便動彈。
輜重壓身?
要不說一個個收成都不差呢!他們收納的物件,再金貴,在西安也不好變現,就都想帶走。可跟著兩宮隨扈上路,哪敢陣勢太張揚了?所以,就想把收成中的銀錢,交我們票莊兌回京城。銀錠多了,太佔地方。
想兌,就給他們兌吧!這也是咱們常做的生意。
擱平常,這還不是例行生意嗎?可現今,他們是只探問,不出手。
為什麼?
咱們的京號遭劫被搶,人家能不知道?現在京號還沒復業,銀錢能匯兌到?
邱掌櫃,硬硬地給他們說:西幫哪能沒京號?朝廷迴鑾之日,必定是我京號劫後開張之時!
何老爺,老號要有這種硬口氣,那倒好辦了。那些權貴們雖是派底下的走卒來打探,我們也不敢大意,但只能含糊應承:大人信得過敝號,我們哪會拒匯?洋人一撤,京號開張,我們立馬收匯。人家也不傻,一聽是活話口,就逼著問準信兒:你們的京號到底何時開張?到底何時能收匯?我哪有準信兒告人家?也只好說:朝廷迴鑾的吉日定了,我們也就有準信兒了。人家說,到那時節,哪還趕得上呀?也是。我們趕緊發了電報,請示老號。老號回電只四字:靜觀勿動。
老號是不大知曉西安近況吧?
我們三天兩頭給老號發信報,該報的都隨時報了。朝廷在這裡,我們哪敢怠慢?可就回了這麼四個字,何老爺,你說叫我們如何是好?
邱掌櫃,你沒聽說吧?孫大掌櫃正鬧著要告老卸任呢,只是老太爺不允。叫我說,孫大掌櫃也真老朽了,放他告老還鄉,天成元也塌不了!
見何老爺說得放肆,邱泰基忙岔開說:老號的事,我們也不便聞聽。何老爺,只求你一解這靜觀勿動的用意,教我們如何張羅?
何老爺又斷然說:邱掌櫃,我看你也別無選擇,就聽我的,硬硬地應承下來!老號叫靜觀勿動,你們也不能回絕人家吧?既不能回絕,那就得應承;既應承,就痛快應承。京城官場這些大爺,你哪敢模稜兩可的伺候?何況這又是他們搜刮的私囊,你不給個痛快話,他哪能放心?
我豈不想如此?可老號不放話,我這裡就放手收了,到時京號不認,或是支付不起,那我們罪過就大了:這不是叫我們砸天成元的牌子嗎?
可你們不應承,也是砸天成元的牌子!這都是些什麼主兒?京城官場的王公大臣,部院權貴!在這非常年頭,想指靠西幫一把,卻指靠不上,想想,以後還能有我們的好果子吃?
何老爺,這其中利害,我能不知道?只是,我們一間駐外分號,哪能做得了這樣大的主?近日,人家都在問:到底何時可開京陝匯兌?老號不發話,我們怎麼回答?
就照我說的,朝廷迴鑾之日,即我天成元京號開張之時!
何老爺,日前我們聽說,朝廷已議定在五月二十一日,起蹕迴鑾。眼看就進五月了,我們也不便再含糊其辭吧?
已議定了五月二十一日迴鑾返京?
這還是聽響九霄說的,禁中消息,他可靈通得很。
何老爺愣住,想了想,忽然擊掌說:邱掌櫃,有好生意做了!
什麼好生意?
四
那天說到關節處,何老爺忽然來了煙癮,哈欠打起來沒完,身上也軟了,什麼話也不想再說。
邱掌櫃是交際場中高手,一看就明白了。以前櫃上也備有煙槍煙土,招待貴客。只是這次返陝後,因西安權貴太多,一個個又似餓狼,就盡力裝窮,不敢招惹。尤其是給西太后底下的崔玉桂,串通響九霄,敲去一筆巨款後,更是乘勢趴下,裝成一蹶不振的氣象。來客不用說大煙招待了,就是茶葉,也不敢上好的。現在何老爺來了煙癮,他還真拿不出救急的東西來。
何老爺,我們真不知你還有此一風雅。怕惹是非,櫃上久未備煙土了,實在不敬得很
什麼風雅?我這是自戕,是自辱,自辱本老爺頭頂的這個無用的功名!
何老爺,叫伙友出去給你張羅些回來?
不連累你們了,本老爺自帶糧草呢。請少候,少候。
邱泰基忙叫伙友扶何老爺進去了,心裡就想,這麼一位商界高手,當日何以要參加朝廷科考?
不由得想到了六爺。何老爺叫開導六爺,可他和這位少東家沒交往過,性情,脾氣,一些兒不摸底,說深了,說淺了,都不好。所以,他也不敢多兜攬,只求六爺在西安平平安安,不出什麼意外就得了。六爺要想拜見官場人物,倒可求響九霄居間引見的。
為盡到禮數,邱泰基派了櫃上一個精幹的伙友,過去伺候六爺。萬一有個意外,也便於照應。可這個伙友跟過去沒多久,就給攆回來了:六爺高低不叫他在跟前伺候。還嫌不夠精幹機靈?六爺說是老太爺有交代,不能太麻煩櫃上。這是託辭吧?何老爺依舊斷然說,人家是不想沾商字的邊兒,就由他吧。
邱泰基還是放心不下:巴結不上倒在其次,為首是怕出意外。住的地界雖然保險,但六爺也不會鑽在那宅子裡不出來。外出遊玩,誰還給他留面子!派個伙友暗暗跟著?
何老爺已經精神煥發地出來了。
邱掌櫃,好生意來了!
什麼好生意?願聽何老爺指點。
這是放在明處的生意,邱掌櫃哪能看不見?
真是看不見,何老爺就給點明了吧!
只要朝廷迴鑾的吉日定了,那我們就有好生意可做!
什麼生意?
邱掌櫃,朝廷迴鑾雖說不上是得勝凱旋,也不會像去年逃出京師時那樣狼狽了。皇家的排場,總是要做足的。這是天下第一大排場,那花銷會小了嗎?官府為辦這份迴鑾大差,必定四處籌措銀子。所以,從迴鑾吉日確定,至兩宮起蹕,這段時日西安的銀根必定會異常吃緊,不正是我們放貸的良機?
良機是良機,可我們拿什麼放貸?西號本來也不是大莊口,架本就不厚,這一向怕再惹禍,儘量趴著不敢動。暗中做了些生意,也撐不起大場面的。尤其老號也不支持,三爺出面都未求來援手。就真是千載難逢的良機,也只好乾瞪眼,動不得。
邱掌櫃,你聽我說!我只說了放貸良機,還未說收存的良機呢!
收存的良機?
邱掌櫃你剛才不是說了嗎?京中權貴正想將私囊中的現銀,交我們匯往京師,這不是小數目,還用發愁無銀放貸?迴鑾花費那是動用京餉官款,權貴們誰捨得動自家的私囊!迴鑾之日越近,他們越著急匯出私銀。我們一手收匯,一手放貸,豈不是好生意!
邱泰基一聽,眼也亮了,說:何老爺,真不愧是京號老手!我們真是給懵懂住了,看西安就只是滿目亂象,卻瞅不出如此良機!
何老爺真是得意,說:邱掌櫃,做票號這一行,你不住一回京號,終是修煉不到家!
這誰不知道?但才具不夠,老號也不會挑你去。不說這種不該說的話了。只是收匯,老號不發話,我們到底不便自作主張吧?京號何日能開張,也須老號做主。聽說京號被糟蹋得片紙不存,底賬也都被搶走了,一時怕也難以恢復吧?
邱掌櫃,你就放心預備做這番好生意吧!老號那邊,本老爺給你張羅!孫大掌櫃聽不進話去,還有康老太爺呢!天成元只要不想關門大吉,就不能不設京號!如今開票號,哪有不設京號的?叫我說,京號實在比老號還要緊。
何老爺既這樣深明大義,我們西號也有救了!還望何老爺能及時說動老號,眼前良機實在是不容遲疑了!
我豈能不知?邱掌櫃你就放心吧。
邱泰基雖未住過京號,但對眼前這一難逢的商機,也已看出來了。只是,老號對西號似乎已有成見,報去的稟帖,再緊急,再利好,也是平淡處理。所以,他才這樣故意裝出懵懂,激起何老爺的興頭,代為說動。何老爺寂寞多年,對商事的激情實在也叫人感嘆。
只是,以何老爺今日之身分,能說動老號嗎?
何老爺知道老號的孫大掌櫃不會買他的賬,就徑直給康老太爺寫了一封信。信走的是天成元的例行郵路,即交付寧波幫的私信局緊急送達。所以,信報還是先到天成元老號,再轉往康莊。
按規矩,外埠莊口寫給東家的信報,老號是要先拆閱的,凡認為不妥的,有權扣押下來。何老爺正是要利用這個規矩,叫老號先拆閱他的信報。因此,他特別囑咐了邱泰基,信皮要與西號慣常信報一般無二,不可露出是他何某人上呈老東家的。
邱泰基就問:這樣經老號過一道手,就不怕給扣押下來?
何老爺說:諒他們也不敢。孫大掌櫃只要讀過我的這道信,他就知道事關重大,絕不敢耽誤;他更會猜想到,老東家見到此信,不會不理睬。這樣一來,他孫大掌櫃對此事也不敢等閒視之了。
邱泰基笑了:何老爺到底手段好,想一箭雙鵰?
何老爺也得意地笑了:實在說,我這信報主要還是寫給孫大掌櫃的,可不把老東家抬出來,他哪會理睬?
邱泰基有意又誇了一句:何老爺真是好手段!
告急的信報就這樣發走了,回音還沒等到,櫃上就來了犯難的事。
這天,邱泰基和何老爺正在後頭賬房議事,忽然就見程老幫跑進來說:響九霄派底下人來了,言明有要事求見邱掌櫃。你快出去招呼吧!
邱泰基沒急著出去,只是說:看這響九霄,排場越發大了!既有要事,怎麼不親自來?只是打劫我們,才肯親自打頭陣?
何老爺倒慌忙說:邱掌櫃,你不想出面,那本老爺出去替你們應付一回!
邱泰基趕緊拉住,說:一個伶人派來的走卒,哪能勞動何老爺!
說著,才出去了。
響九霄底下的這個走卒,居然也派頭不小,見面連個禮也不行,仰臉張口就問:你就是邱掌櫃?
邱泰基心裡有氣,面兒上不動聲色,忙行了一個禮,說:不知是公公駕到,失敬了,失敬!
那走卒見此情形,忙說:邱掌櫃認錯人了,我是郭老闆打發來的
邱泰基才故意問:郭老闆?就是唱戲的郭老闆?
對。
小子,你把我嚇了一跳!去年,西太后跟前的二總管崔公公,親臨敝號,還沒你小子這派頭大呢!人家也還講個禮數,更沒這麼仰臉吊脖子的跟人說話。你這副派頭,我還以為是太后跟前的大總管李公公來了!
那走卒聽不出是罵他,倒呵呵笑了。
邱泰基拉下臉,厲聲說:小子,你聽著!我跟你家郭老闆可是老交情了。以前我沒低看他,如今他也沒低看我。今日就是他親自上門,也不會像你小子這麼放肆!郭老闆現在身價高了,你們這些走卒也得學些場面上的規矩,還生瓜蛋似的,那不是給你們主子丟人現眼嗎?等見著郭老闆,我得跟他當真說說!
那走卒這才軟了,忙跪下說:邱掌櫃在上,小人不懂規矩,千萬得高抬貴手,別說給郭老闆知道!
怎麼,你們郭老闆也長脾氣了?
可不是呢!邱掌櫃要把剛才的話,說給我們班主聽,那小人就得倒灶了
我還當你小子膽子多大呢!郭老闆派你來做甚,起來說吧。
小人有罪,就跪著說吧。我們班主交給我一張銀票,叫面呈邱掌櫃,看能不能兌成現銀?說時,就從懷中摸出那張銀票,雙手舉著,遞給了邱泰基。
邱泰基接過來細看,是天成元京號發的小額銀票,面額為五百兩銀子。京中這種小票,其實也是一種存款的憑證,只是因數額少,就寫成便條樣式,隨存隨取,也不記存戶姓名。不想,這倒十分便於流通,幾近於現代的紙幣了,在京中極受歡迎。但這種小票也只是在京城流通,京外是不認的。響九霄在西安土生土長,他哪來的這種小票?是哪位權貴賞他的吧?
邱泰基就問:這張銀票,是誰賞你們郭老闆的?
那走卒說:銀票不是我們班主的,聽說是位王爺託班主打聽,看這種銀票在西安管用不管用?
知道是哪位王爺嗎?
班主沒交代,小人哪能知道?
那你記清了:這種票是我們天成元寫出的,不假。可它是銀票,不是匯票。我們票莊有規矩:只收外埠的匯票,不收外埠的銀票。
邱掌櫃是說,這種銀票不管用了?
這張銀票是我們京號寫的,在京城管用,在西安不管用。不是我們寫的票,辨不出真偽,不敢認。你回去告訴郭老闆,這銀票廢不了,妥為保管吧,等回到京城,隨時能兌銀子。記清了吧?
記清了!
這時,何老爺走了出來,說:拿銀票來我瞅瞅。
邱泰基把銀票遞了過去,說:你看是咱京號的小票吧?
何老爺只看了一眼,就說:沒錯,可惜是光緒二十二年寫的票,那時本掌櫃已離開京號了。
邱泰基說:誰呀,逃難還把這種小票帶身上?
何老爺說:人家不是圖便當嗎?總比銀子好帶。說著,就轉臉對那走卒放出斷然的話來:回去跟你們主子說,銀票我們認,想兌銀子就來兌!
邱泰基一臉驚異,正要說什麼,何老爺止住,搶著繼續說:按規矩,我們西號不能收京號的銀票,可遇了這非常之變,敝號也得暫破規矩,為老主顧著想。既然朝廷落腳西安,我們西號就代行京號之職,凡京號寫的票,不拘銀票匯票,我們都認!聽清了吧?
那走卒也是一頭霧水,瞅住邱泰基說:聽是聽清了,這位掌櫃是
何老爺又搶先說:本掌櫃是從天成元老號來的,姓何,早年就在京號當掌櫃!小客官,要不把這五百兩銀票給你兌成銀錠?背了現銀回去,也省得你家主子不信我們,又疑心你!
那走卒忙說:班主只叫來問問銀票管用不管用,沒讓兌銀子。
何老爺緊跟住就說:那你還不趕緊去回話!
那走卒慌忙收起銀票,行過禮,出門走了。
邱泰基早忍不住了,跺了跺腳,說:何老爺,你不是害我們呀!
何老爺一笑,說:天大的事,咱們也得到後頭賬房說去,哪能在鋪面吵?
來到後頭,何老爺立刻一臉正經,厲色說:
邱掌櫃,我可不是擅奪你們的事權,此事是非這樣處置不可!這張銀票,事關重大!
邱泰基有些不解:區區一張小票,有什麼了得?
邱掌櫃,你忘了眼下是非常之時?
非常之時又如何?
就我剛才那句話:現在你們西號,就是平素的京號!
我們哪能擔待得起?再說,老號也沒把我們當回事。
邱掌櫃,調你回西安,為了什麼?還不是西安莊口非同尋常嗎?
這我知道,我也想將功補過。
我告你,眼下就是一大關節處!稍有閃失,就難補救了。
邱泰基這才忽有所悟,忙恭敬地說:願聽何老爺指點!
五
那時已將近午飯時,邱泰基就叫司廚的伙友加了幾道菜,燙了壺燒酒,還邀來程老幫,一道陪何老爺喝酒。被這樣恭維著喝了幾盅酒,何老爺也沒得意起來,依然一臉嚴峻。不等邱泰基再次請教,何老爺就指出了眼前的要緊處。
原來,西幫的京號生意,除了兜攬戶部的大宗庫款,另一重頭戲,就是收存京師官場權貴的私囊。京官的私囊都是來路曖昧的黑錢,肯交給西幫票號藏匿,自然是因為西幫可靠。首先守得住密,其次存戶日後就是塌台失勢了,也不會坑你。所以,京官的私囊黑錢,存入票號比藏在府中保險得多,不用擔心失盜,連犯事抄家也不用怕。西幫原本不過是用此手段拉攏官場,不想竟做成了一種大生意。滿清時代官員的法定俸祿非常微薄,就是京中高官,真清廉起來,那可是連套像樣的行頭,也置辦不齊的。既然不貪斂搜刮不能立身,那貪起來也就無有限度。京師官多官大,西幫京號吸納這種私囊黑錢可謂滔滔不絕!
去年遭遇塌天之禍,京師陷落,西幫京號自然也無一家能倖免。京號遭了洗劫,心痛的就不只是西幫的財東掌櫃,那些存了私囊的官場權貴更心痛得厲害。只是當時局面危急,先顧了逃難保命。現在和局定了,返京指日可待,這些主兒自然惦記起他們的存銀來了。
託人拿銀票來探問,就是想摸摸我們西幫的底細:你們還守信不守信?被洗劫去的銀錢,你們能不能賠得起?
程老幫就說:要摸底,那得去尋京號、老號,我們哪能做得了這種主?
何老爺說:我們天成元也是匯通天下一塊招牌!現在尋著你們西號,也就是把你們當京號、老號。你們一言不慎,即可壞天成元名聲,乃至西幫名聲!
邱泰基驚問:這麼嚴重?
何老爺說:眼下是非常之時,一切都不比往常。就拿今日這張京號小票說,我們一推脫,告人家回到京城再商量,人家準會起疑心:你們天成元遭劫後已大傷元氣,恐怕指靠不上了吧?這種疑心在市間蔓延開來,那會是什麼局面?首當其衝,你們西安莊口就可能受到擠兌!西安一告急,跟著就會拉動各地莊口!我們天成元一告急,很快也要危及西幫各號!當年胡雪巖的南幫阜康票號,不就是這樣給拉倒的嗎?
程老幫說:阜康受擠兌,是胡雪巖做塌了生意。我們遭劫,可是受了朝廷的連累,又不是做塌生意了。這回是天下都遭劫,也不至獨獨苛求我們西幫吧?
何老爺說:正是天下遭了大劫,人心才異常惶恐,稍有一點風吹草動,都會釀成滔天大浪!尤其這班京官,他們一起騷動,市間還能平靜得了?
邱泰基說:這樣說來,不只是我們天成元一家受到試探吧?
何老爺說:那當然了。兩位可多與西幫同業聯絡,叫大家都心中有數。在西安,我們西幫票商有無同業會館?京師、漢口、上海這些大碼頭,都有我們的票業會館,或匯業公所。
邱泰基說:以前張羅過,未張羅起來。
何老爺就說:那就趕緊聯絡吧。
邱泰基問:何老爺,大家當緊通氣的,該有些什麼?
當緊一條,必須硬硬地宣告,西幫的京號一準要恢復開張!京號舊賬一概如常,不拘外欠、欠外,都毫釐不能差。持京號小票的,如急用,可在西安兌現。如此之類吧,不要叫市間生疑就是。
程老幫說:都持京號銀票來兌現,豈不要形成擠兌之勢?我們只怕也應對不了
何老爺說:眼看要踏上回京的千里跋涉了,他們兌那麼多銀子做甚!何況,當時從京城逃出,大概也沒顧上帶出多少這種小票吧?所以,盡可放出大話去。再者,凡要求往京城匯銀子的,我們盡可放手收匯!匯水呢,也不宜多加。官府來借款,也盡力應承!在這種危難惶恐之秋,我們不可積怨於世。
邱泰基說:高見,我們就聽何老爺的!只是,還得請你再與老號通氣,當前西安的要緊處,老號未必能深察到。
何老爺說:這不用你們操心,本老爺會再謀妙著,說動老號。既然和局成了,朝廷回鑾之期也定了,老號張羅京號復業,就該刻不容緩。不能叫你們在西安唱空城計呀!
邱泰基說:京號的戴老幫還在上海嗎?
何老爺說:還在上海。不過,眼前局勢,戴老幫也會早一步看清的,回京如何作為,只怕他也是成竹在胸了。
程老幫問:以何老爺眼光看,老號孫大掌櫃真告老退位,京號的戴掌櫃會繼任領東大掌櫃嗎?
何老爺笑了笑,說:換領東大掌櫃,在東家也是一件大事,本老爺哪敢妄言?眼下天成元另有一個重要人位,我倒是敢預測一番。
邱泰基就問:哪一個人位?
何老爺說:津號老幫。自前年劉國藩自盡後,這個人位就一直空著。這次津號遭劫更甚,不派個得力的把式去,津號很難復興的。
邱泰基說:事變前,老號不是要調東口的王作梅去津號嗎?
何老爺說:此一時非彼一時。東口所歷劫難也前所未有,王老幫怎能離得開?東口字號,也並不比津號次要,老號才不敢顧此失彼。所以,津號老幫必然要另挑人選。
程老幫說:天津衛碼頭本來就不好張羅,這次劫難又最重,誰去了也夠他一哼哼。
邱泰基說:何老爺你挑了誰去?
何老爺說:要能由我挑,那我可誰也不挑,只挑本老爺我自家。哈哈,哪有這種美事!我是替老號預測:津號新老幫,非此人莫屬!
邱泰基就問:何老爺預測了誰?
何老爺一笑,說:還能是誰,就是邱掌櫃你呀!
邱泰基一愣,說:我?但旋即也笑了。何老爺不要取笑我!
何老爺卻正經說:我可不是戲言!
邱泰基也正色說:不是戲言,那也是胡言妄說了。我有大罪過在身,老號決不能重用的。
何況,這一向孫大掌櫃對我也分明有成見。再則,我自家本事有限,張羅眼前的西號都有些慌亂,哪能挑得起津號的重擔?
何老爺卻問程老幫:你看本老爺的預測如何?
程老幫說:邱掌櫃倒真是恰當的人選。只是,老號能如何老爺所想嗎?
邱泰基更懇求說:何老爺,此等人位安排,豈是我等可私議的?傳出去,那可就害了我了!
何老爺笑了,說:此言只我們三人知道,不要外傳就是了。等我的預言驗證之日,邱掌櫃如何謝我?
邱泰基也笑著反問:如不能應驗,何老爺又如何受罰?
何老爺說:那就請程老幫做中人,以五兩大煙土,來賭這件事,如何?
邱泰基說:我又沒那嗜好,要大煙土何用?
何老爺說:大煙土還不跟銀子一樣!
說到這裡,何老爺又來了煙癮,也就散席了。
但何老爺的這一預言,卻沉沉地留在了邱泰基的心頭。做津號老幫,他哪能不嚮往?只是自前年受貶後,他幾乎不存高昇的奢望了:因淺薄和虛榮,已自斷了前程。去年意外調他重返西安,心氣是有上升,卻也未敢生半分野心。熬幾年,能再做西號老幫,也算萬幸了。三爺對他的格外賞識,倒也又給他添了心勁。可去做津號老幫,他是夢也不敢夢的。
何老爺放出此等口風,或許是聽三爺說了什麼吧?
三爺雖接手掌管了康家商務,可真正主事的,依舊還是老太爺:這誰不知道!三爺即使真說了什麼,何老爺也敢當真?
何老爺中舉後就瘋瘋癲癲的,他的話不該當回事吧。但何老爺來西安後,無論對時局對生意,那可真是句句有高見,並不顯一點瘋癲跡象。
在這緊要關頭,把何老爺派到西安來指點生意,或許是康老太爺不動神色走的一步棋?
那何老爺關於津號老幫的預言,還或許是老太爺有什麼暗示?
看何老爺那一副瞭然於胸的樣子,也許真
邱泰基正要往美處想,忽然由津號聯想到五爺五娘,不由在心裡叫了一聲:不好!
他猛然醒悟到,這麼多天,只顧了與何老爺計議商事,幾乎把六爺給忘了!六爺沒有再來過櫃上,他和程老幫也沒去看望過六爺。真是太大意了!
六爺不會出什麼事吧?
邱泰基立馬跟程老幫交代了幾句,就帶了一名伙友,急匆匆往六爺的住處奔去。
六
到了那宅子,還真把邱泰基嚇慌了:六爺不但不在,而且已有幾天未回來了!
老天爺,出了這樣的事,怎麼也不跟櫃上說一聲?
這次出來跟著伺候六爺及何老爺的,除了桂兒,還另有三個中年男僕。何老爺住到櫃上,六爺叫帶兩個男僕過去使喚,何老爺一個也不要。他說住到字號,一切方便,不用人伺候。四個僕人都跟著六爺,但他外出卻只帶了桂兒一個小僕。問為什麼不多跟幾個去,僕人說六爺不讓。
六爺出去時,也沒說一聲,要去哪?
六爺交代,要出西安城,到鄰近的名勝地界去遊玩。我們說,既出遠門,就都跟著伺候吧?桂兒說,不用你們去,你們去還得多僱車轎,就在店裡守好六爺的行李。我們問,出去遊玩,也得有個地界吧?桂兒說,出遊還有準?遇見入眼順心的地界,就多逛兩天,遇上沒看頭的,就再往別處走吧。桂兒這麼著,那是六爺的意思。我們做下人的,能不聽?
你們都比少東家和桂兒年紀大,出門在外,哪能由他們任性!眼下正是亂世,放兩個少年娃出城遊玩,就不怕有個萬一?
我們也勸了,勸不住呀!
你們勸不住,跟我們櫃上說一聲呀!還有何老爺呢,何老爺跟來不就是為管束六爺嗎?
他們早也沒說,臨走才交代我們,交代完抬腳就走了。我們哪能來的及去稟告何老爺?
他們走後,也不能來說一聲?
我們覺著不會有事。何老爺總說,朝廷在西安,什麼也不用怕。
你們真是!六爺走了幾天了?
今兒是第四天了。
雇的是車馬,還是轎?
跟車行雇的標車。
你們誰去雇的?
桂兒雇的。
帶的盤纏多不多?
帶了些,也沒多少。
再問,也還是問不出個所以然來。邱泰基只能給他們交代:有六爺的消息,趕緊告櫃上,但也不用慌張,更不能對外人說道此事。
邱泰基趕回字號說了此情況,程老幫也驚慌了,但何老爺卻只是恬然一笑,說:由他遊玩去,什麼事也沒有!
邱泰基說:處此多事之秋,總是讓人放心不下。萬一
何老爺還是笑著說:只要邱掌櫃在西安沒仇人,就不會有萬一!
邱泰基忙說:我和程老幫,在西安真還沒有積怨結仇。
何老爺就說:那就得了,放寬心張羅生意吧。現在西安滿大街都是權貴,哪能顯出六爺來!再說,既已過去三四天,要出事,也早出了,綁匪的肉票也該送來了;肉票沒來,可見什麼事也沒有。
程老幫慌忙嚷道:何老爺快不敢說這種不吉利的話了!等肉票送來,那什麼也來不及了!
何老爺只是笑,不再說什麼。
何老爺說的也是,真要出了事,也該有個訊兒了。邱泰基也就不再多說什麼,但心裡還是鬆寬不了。託鏢局的熟人在江湖上打探一下?也不太妥當,萬一傳出什麼話去,以訛傳訛,好像天成元的少東家又出了事,豈不弄巧成拙!他只好暗中吩咐櫃上的幾位跑街,撐長耳朵,多操心少東家的動靜。
然而,又過了兩天,還是什麼消息也沒有。邱泰基再也坐不住,連何老爺也覺得不對勁了,不斷催問有消息沒有。
此時的六爺,正離開咸陽,往西安城裡返。要照他的意思,才不想回去呢:正是甜美的時候!但孫小姐怕耽擱太久了,叫人猜疑,主張先回西安住幾天,再出來。六爺也只好同意。
當初,由太谷到達西安剛住下來,六爺就急忙命桂兒去打聽,看孫小姐到了沒有。桂兒經這一路長途勞頓,動都不想動了,就說孫家一行晚動身,一準還沒到,就是明兒出去打聽,也一準白跑。
六爺連罵了幾聲小懶貨,桂兒還是不動。六爺只好美言相求,並許予重賞,桂兒這才不情願地去了。
孫家在西安也有幾處字號,其中一間茶莊尤其出名。這間茶莊字號老,莊口大,鋪面排場,後頭也庭院幽深,地界不小。當時西安講究些的客棧不易賃到,孫家就吩咐茶莊,在字號後頭拾掇出一處小院,供小姐臨時居住。所以,孫小姐在行前就跟六爺這邊約好了,到西安後去茶莊聯絡。
桂兒尋到孫家茶莊,繞到後門,就按約定對門房說:我是天成元駐西安的夥計,聽說孫小姐要來西安,我們掌櫃叫來打聽一下,小姐哪天能到,討個準訊兒,我們好預備送禮。
哪想,門房上下瞅了瞅桂兒,竟說:東家二小姐,早已經到了。
已經到了?桂兒吃驚不小:孫家怎麼倒跑到前頭了!
可不是,已經到了兩天了。
麻煩稟報一聲,能見一見孫小姐底下的人嗎?
門房又上下瞅了他一遍,就進去傳了話。
跑出來的一個小僕,桂兒認得,是跟孫小姐的,叫海海。但海海裝著不認得他,繃著臉叫桂兒跟他進去。進去,也沒叫見孫小姐,只停在過道說:你們走得也太慢了!告你們六爺,明兒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