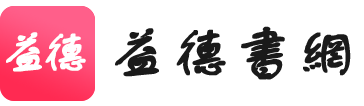謝謝你,子奇,你解除了我的一塊心病!她說,在這以前,我從來也沒有這樣問過你,我不敢問。當我熾烈地愛著你的時候,我也曾經在眼前看到了璧兒,她是你的妻子,是我的姐姐,我擔心自己的舉動傷害了她。可是,愛是不顧一切的,感情衝破了理智,我讓自己不去想她,不去想後果,我們相愛了。但我心中仍然有一種莫名其妙、時隱時現的歉疚,對她的歉疚,這種情感牽著我回來,離家越近,就越強烈了。我並不是來向她道歉,也不是來接受她的懲罰,而是要要獲得心理上的解脫,現在,你給我解脫了,把我對她的歉疚,解脫了!
可是,這一切又怎麼向她解釋呢?韓子奇並不感到輕鬆,對她說,我不愛她了,從來就沒有愛過她?她會怎麼想呢?不,她根本不理解我們!她只能認為我是喜新厭舊,拋棄糟糠之妻!
她愛怎麼想就怎麼想吧,你又不是賣給她終身為奴,走自己的路吧!我們離開她,把房子、財產、這兒的一切都留給她,我們問心無愧、兩手空空地去開闢自己的家!梁冰玉心中已經做出了決斷,子奇,奇哥哥,我們走!
走?往哪兒走?整個北平哪兒都有我的熟人,想找個藏身之地,辦得到嗎?人言可畏,社會輿論能殺人!韓子奇感到為難,那雙佈滿血絲的眼睛閃爍著憂愁和恐懼,而且,她也不會答應!
那麼,我們就離開北平,離開中國,回倫敦去!梁冰玉重新激起了遠行的念頭,遠遠地離開她,彼此無干無涉了,誰也不欠誰的,誰也沒有對不起誰的了,我們去尋找自己的歸宿,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事業!我們走吧!
韓子奇沒有回答,緩緩地垂下頭,雙手支著沉重的額頭。
怎麼?你不想走?
我
不敢走?梁冰玉微張著嘴,吸進一股絲絲的涼氣,她覺得自己那顆灼熱的心在收縮,在冷卻。
走?韓子奇一想到走,就看到了一雙雙的眼睛,梁君璧的眼睛、天星的眼睛、姑媽的眼睛、全北平人的眼睛,都在盯著他,問他:你走?你哪兒走?你敢走?你憑什麼走?他無言以對,他不寒而慄!
你沒有這個膽量?梁冰玉的心越來越冷了,在海外相依為命十年的韓子奇,使她感到陌生了。這是那個在倫敦的玉展中當著幾千名觀眾用英語做滔滔不絕的演講沒有片刻的猶豫和絲毫的驚慌的韓子奇嗎?是那個不為利誘所動、斷然拒絕出售他的藏品、毫不可惜地丟掉成為百萬富翁的機會的韓子奇嗎?是那個耗盡了心血供她就讀牛津大學、把滿足她的願望作為自己的最大欣慰的韓子奇嗎?是那個在戰爭災禍中用熾烈的愛溫暖了她的心、拯救她的人生的韓子奇嗎?是那個徹夜守在產房門口、聽到新月的第一聲啼哭而欣喜若狂的韓子奇嗎?應該是啊,怎麼會不是了呢?紛亂的思緒使她覺得這個韓子奇似是而非,變得模糊了,不易辨認了,也許她過去看到的一切都是錯覺?也許是他在一夜之間改變了面目?也許世界上本來就存在兩個韓子奇?她不敢再往下想了!你準備怎麼辦?她問他,心在不安地悸動,總不能真像她們說的那樣,娶兩個老婆吧?
我我糊塗啊!韓子奇陷入了無法排解的矛盾之中,用拳頭打著自己的腦袋,我們不該回來,不該回來!
你不必這樣衝動,打壞了自己也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梁冰玉撥開他的拳頭,我們不是小孩子打架,意氣用事沒有用處,我在誠心誠意地跟你商量事兒呢,這將決定我們的命運!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你說吧,我聽你的
我哪能讓你聽我的?你有權利決定自己的生活道路。何況,我要說的都已經說了,你都並不贊成啊!
我唉!韓子奇仰面長嘆,我為什麼要回來啊!
韓子奇顧左右而言他,極力迴避他無法迴避的抉擇。梁冰玉心目中的那個頂天立地、有膽有識的男子漢,像冰山一樣融化了,坍塌了。滿懷希望的人往往易於衝動,一旦失望了,反而倒冷靜了,是啊,你到底為了什麼才回來的?
他不語,呆呆地望著頂棚。
是為了這所宅子,為了奇珍齋,為了運回那批寶貝?
我不能失去這一切!玉,是我的生命
是為了把玉王的旗號打回北平,重新開始你的事業?
我不能沒有我的事業,我的事業在中國
是為了保住這個家,不讓天星成為沒有父親的孤兒?
是是吧?天星,可憐的天星!
還為了讓你的妻子不至於失去當家的?
哦他噎住了。
你答應啊,你應該說是啊!這一切都是明擺著的!她望著他,等待回答,你不愛她,可又不能、也不敢離開她!
玉兒,他惶然地說,是我們都想想家,才回來的
家?家是你的,一切都是你的!走了都丟掉了,回來又都有了,你什麼也沒失去!
啊,奇珍齋已經倒閉了!他淒楚地說。
噢,你也有損失?她一個嘆息,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別難過,你的那些寶貝還在,博雅宅還在,你的老婆孩子還在!你的家沒毀,你應該回來!可是,這兒還有我的什麼?我幹嗎要跟著你往這兒跑啊?她愣愣地望著前面,茫然張開兩隻手,像問那頂棚,問那牆壁,問那窗紙,幹嗎要往這兒跑啊?
玉兒,你他惶惑地轉過臉,你是怎麼了?這兒也是你的家呀
我的家?我的家沒有了!她頹然垂落兩隻空空的手,撫在自己的膝上,沒有了!我的家在奇珍齋後院那低矮的小房裡,窗外有陽光,有花兒,石榴、牽牛、草茉莉、指甲草,很香呢;屋裡有溫暖,媽媽給我做糖餑餑、豆沙包兒,很甜呢;夢中有催眠曲,爸爸深夜還在磨玉,沙,沙很美呢。可惜都沒有了,我再也沒有那個家了,只留下美好的回憶!那個家,雖然貧困、狹小,生活得艱難,可我總也忘不了啊!沒有了,沒有了
梁冰玉自憐自嘆,憂傷的眼睛充盈了淚水,無聲地墜落下來。她不去拂拭,讓冰冷的淚珠流過面頰,澆滅心頭那一點殘焰。
韓子奇站起身來,撫著她的雙肩。掏出身上的手絹兒,為她擦去淚痕,玉兒,我求你別這麼傷感,這兒永遠是你的家!
她撫住他的手,男子漢的手,似乎又讓她感到了力量的存在。是嗎?她吻著那隻手,眼淚流在他的手上,不,奇哥哥,這兒不是我們的家了,我們走吧,為了你,為了我,為了新月!
她感到那隻手在痙攣。
你為什麼非得走呢?他說,聲音很低,很弱,就不能先忍耐忍耐嗎?
忍耐?你叫我怎麼忍耐?低眉順眼,向她就範,裝做回來住娘家?讓新月叫你姨父、舅舅?等找著主兒打發我改嫁?是嗎?
他不語,顫抖的手撫摸著她的頭髮。
梁冰玉猛地甩掉他的手,推開他,站起身來:韓子奇啊韓子奇,你也算個男人?
韓子奇一個趔趄:玉兒
這兒沒有玉兒,站在你面前的是梁冰玉!
冰玉,你聽我說
不必說了,過去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我只想告訴你:我是一個人,獨立的人,既不是你的、更不是梁君璧的附屬品,不是你們可以任意擺佈的棋子!女人也有尊嚴,女人也有人格,女人不是男人錢袋裡的鈔票,可以隨意取,隨意花;女人不是男人身上的衣裳,想穿就穿,想脫就脫,不用了還可以存在箱子裡!人格,尊嚴,比你的財產、珍寶、名譽、地位更貴重,我不能為了讓你在這個家庭、在這個社會像人而不把我自己當人!你為了維護那個空洞虛弱的軀殼,把最不該丟掉的都丟掉了!十年了,我怎麼沒有認識你?瞭解一個人,愛一個人,是多麼艱難?你說你不後悔和我的結合,我不知道這話是不是真誠的,但是我現在後悔了,我錯了,從頭到尾都錯了!我還以為我得到的是愛呢,還以為你這個男子漢的肩膀能擔起愛的責任呢,原來你也和她一樣,根本不懂得什麼是愛情!我錯了,完全錯了!
梁冰玉不再流淚,沒有淚水的眼睛更清亮了;她不再痛苦,痛苦都已經過去了。十年認識了一個人,三十年懂得了人生,這不也是付出的歲月換取的收穫嗎?她比過去聰明一些了,她不再糊塗了!
不,冰玉,是我錯了!韓子奇無力地支撐在寫字檯旁,他悔恨交加,痛徹肺腑,捶打著自己的胸膛,一切都是我的錯,是我毀了你!
這話倒大可不必說了吧?也許是我毀了你呢?你有這麼好的一個家,有老婆,有孩子,還有豐厚的財產,我不能讓你一敗塗地!梁冰玉心平氣和,冷靜得如同一潭微波不起的湖水,我給你添了那麼大的麻煩,實在是對不起了!沒有了我,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我該走了,不打擾你們了!
真要走嗎?這不堪設想的打擊真的落到了韓子奇的頭上,落到了他的心上,他感到自己的心臟和整個身體都在驟然下沉,彷彿腳下是無底深淵、萬丈波濤,他不知道一旦失去梁冰玉,他將怎樣生活?他像一個行將溺死的人,本能地要呼救,要求援,奔過去抓住梁冰玉的手,冰玉,你不能走,我離不開你!
你,也離不開這個家啊!梁冰玉冷冷地抽出自己的手,不要這樣,生活中又不能演戲,我不希望悲悲切切地分手,平靜些,讓我們微笑著向過去告別!
韓子奇喪魂失魄地站在那裡,終於無可奈何地垂下了頭,那寬寬的肩腫,高大的身軀,像拆散了所有的骨節,鬆垮了!你打算去哪兒?是去倫敦的華人學校繼續教書?還是找亨特先生
這,你就不必操心了,天下之大,總能有我容身的地方,女人沒有男人的保護也能活!既然我們錯誤的結合是羅網,是牢籠,那麼,擺脫了它,就是一個自由身了,這是我用過去的生命換來的,我將珍惜它!我相信我的餘生是快樂的,有新月給我做伴,我就是最幸福的人了!
什麼?新月?你還要把新月帶走?韓子奇那鬆散的軀體在戰慄,別,別帶走她,我不能再失去新月,她是我的女兒!是我們愛情的結晶
愛情?什麼是愛情?天底下有真正的愛情嗎?也許值得我愛的只有自己的女兒!我的女兒,我當然要帶走,免得落在別人手裡當個耶梯目,也省得你為難啊!
不!新月永遠是我的女兒,你給我留下她!我求你了!韓子奇顫抖著,撲通跪在了地上!
院子裡倒是好熱鬧,這邊兒,新月和天星又玩兒上了騎大馬,十一歲的天星自然是馬了,讓妹妹騎在身上,從後院跑到前院,騎的和被騎的都開心之至!那邊兒,韓太太和姑媽正吭吭哧哧地把擱在倒座裡的大箱子往上房裡頭搬,這是家業,是命,是比什麼都又重的,把這些鎖在家裡,就把韓子奇拴住了,他哪兒也走不了啦!西廂房的那番私房話,是韓太太故意給他們閃開的空兒,讓他們嘰咕去,能嘰咕出個什麼來?至大也翻不出我的手心兒去!
博雅宅裡,陽光燦爛,喜氣洋洋,西廂房裡的狂風巨浪並沒有發出多大的聲響。
新月在度過有生以來最愉快的一個下午,她揪著哥哥的脖子,一顛兒一顛兒地享受走馬逛北平的樂趣,天星一邊爬著、蹦著,還氣喘吁吁地唱著數來寶:
平則門,拉大弓,
過去就是朝天宮。
朝天宮,寫大字,
過去就是白塔寺。
白塔寺,掛紅袍,
過去就是馬市橋。
馬市橋,跳三跳,
過去就是帝王廟。
帝王廟,搖葫蘆,
過去就是四牌樓。
四牌樓東,四牌樓西,
四牌樓底下賣估衣。
夜深了,西廂房裡,新月躺在媽媽年輕的時候睡過的床上,在媽媽的輕輕拍撫下,甜甜地睡著了。她做了一個長長的夢,色彩斑斕的夢:倫敦的塔橋,北平的大前門,海上的大輪船,雕花影壁上的月亮,又香又甜的薄脆,都湊到一起來了,惟獨沒有夢見早晨進家之後的那一場大人的爭吵。她在夢裡還格格地笑呢,她夢見的都是美好的。夢總是美好的。夢應該是美好的。
梁冰玉哄睡了孩子,在煤油燈下準備自己的行裝。沒有什麼可以準備的了,怎麼來的,還是怎麼離開,她的小皮箱裡的一切,還要隨著她做無根飄萍。但是,她必須把新月的東西留下。她終於答應把新月留下了,為了韓子奇那聲淚俱下的哀求,為了他那七尺之軀的屈膝下跪。父女之情,也許不會是虛假的吧?她擔心沒有新月,韓子奇將會不久於人世感情的失落是摧殘人生最烈的毒劑。留下吧,母親的心肝從此將要摘下來了,這一次離別,又是天涯海角,也許今生今世都沒有母女重逢了!
她細細地理好新月的衣服、鞋襪、手絹兒,恨不能把一切都給女兒留下,連同她那顆慈母心!
再也沒有什麼了,她要闔上小皮箱了,又被箱蓋裡面布兜兒裡的一隻小小的鏡框擾亂了心。她取出那隻鏡框,上面鑲著一幅照片,是她和新月的合影,告別倫敦之前,在唐人街的一家照相館照的,她特地換上了中式旗袍。這是她們母女僅有的一張合影。為什麼不多照一些呢?唉,沒有,她教書太忙了,總以為以後有的是時間,不料,卻再也沒有了,這張照片竟是最後的一點紀念。帶走吧,好時時能看見新月;不,留下吧,讓新月時時能看見媽媽,好像媽媽沒有走,媽媽永遠留在她身邊,陪著她!
她把照片放下了,放在寫字檯上。明天早上,新月一睜眼就能看見媽媽;以後的漫長的歲月裡,還有無數個早晨,無數個白天,無數個夜晚,媽媽都在這兒守著新月!
女兒睡得真香,真穩,因為有媽媽在身邊。可是,明天,明天媽媽就不在了!她俯下身去,躺在女兒的身邊,把女兒摟在懷裡,緊緊地,臉貼著臉,手拉著手,心連著心。不,女兒怎麼會知道此時此刻媽媽的心呢?她不知道,她永遠也不會知道,但願她不要知道吧!
她坐起來,從小皮箱裡抽出幾張信紙,捻亮煤油燈,感情的洪水在筆下湧流,她給女兒留下了一封字字和著淚水的信,這封信,她將封起來,交給韓子奇,要求他答應她最後一點也是唯一的囑託:永遠也不要對新月提起我,不要讓她感到自己是個沒有媽媽的孩子,等到她長大成人,念完了大學,再把這封信交給他!
第二天,天色還沒有破曉,上房臥室裡,韓太太朝著聖地麥加的方向,虔誠地做晨禮。
姑媽滿臉是淚,輕輕地走到她的身後。我說姑媽真是糊塗了,竟在這個時候來打擾她,咱姐兒倆再商量商量,非得把玉兒趕走不成嗎?
不能留她了!韓太太喟然嘆息,她造的這罪,退一萬步說,就是我能容,教規也不容啊!
誠然,梁冰玉是有罪的,韓子奇是有罪的。他們的結合,沒有古瓦西,沒有證婚人,沒有婚書,也沒有舉行宗教儀式,當然是非法的,是真主和穆斯林所不能容忍的!在穆斯林世界,已婚者犯通姦罪和殺人、叛教並列為三大不可饒恕的罪惡,《古蘭經》明確訓示:淫婦和姦夫,你們應當各打一百鞭。你們不要為憐憫他倆而減免真主的刑罰,如果你們確信真主和末日。更何況,梁冰玉和韓子奇是什麼關係?她是他的合法妻子的親妹妹,《古蘭經》中赫然載有這樣的戒律:真主嚴禁你們同時娶兩姐妹!
她得走!走得越遠越好,永世也別回來了!兩行熱淚從韓太太蒼白的臉上流下來。驅逐情同手足的妹妹,她也是痛苦的,但除此之外,還能有什麼辦法呢?
其實,即使她挽留妹妹,梁冰玉也決不會留下了,她非走不可,現在就要啟程了。她不能等到天亮,不能看著女兒醒來,一聲媽媽,會斷送她的一切,她必須走了!
她最後再親親女兒的臉
該走了,再也不能停留了!
梁冰玉跨出博雅宅的大門,迎著寒風、踏著夜色走去了,連頭都沒回。她把這裡的一切都忘了,耳邊只縈繞著一個聲音:媽媽
媽媽走了,新月還在夢中。
媽媽是在夜裡走的,那個夜晚很黑,很冷,沒有月亮。農曆的二月初三,天上的新月還沒有出來。